潮评丨科技创新让文物活起来
潮评丨科技创新让文物活起来
潮评丨科技创新让文物活起来“不会考古的(de)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。”搞了几十年外国考古,访问(fǎngwèn)和发掘过(guò)的国家(guójiā)能绕地球一圈,这样的学者寥寥无几。54岁那年,考古学者张良仁又一次“尝鲜”,主动玩起短视频,并用两年时间成为全网拥有200万“粉丝”的美食博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(wǒ)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(hé)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’起来。”从“探墓”到“探店”,巨大跨界背后,是一位不善言辞的学者对(duì)自己专业的热爱。当学术与大众(dàzhòng)紧密联系在一起(yìqǐ)时,张良仁更加笃信自己的选择和付出。
 “严格意义上讲,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。第一(dìyī),我不会做饭;第二,我吃包子也好(yěhǎo),吃别的食物也好,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、怎么做出来的,我讲不清楚。我能讲讲这种食物、食材、烹饪技术是(shì)起源于什么年代的,怎么发展的,比如(bǐrú)陶器怎么发展的,食材怎么演变来的。这是我擅长的东西,因为(yīnwèi)我在做考古。”
4月19日,南京大学考古学者张良仁教授在北京举行(jǔxíng)的《吃的中国史》新书分享会上,与读书博主赵健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仁湘(xiāng)共同探讨美食(měishí)与历史的关系。在分享会上,张良仁用(yòng)一段自谦之语开场,而在网络上,他则将“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”作为自己的“标签”。
“严格意义上讲,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。第一(dìyī),我不会做饭;第二,我吃包子也好(yěhǎo),吃别的食物也好,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、怎么做出来的,我讲不清楚。我能讲讲这种食物、食材、烹饪技术是(shì)起源于什么年代的,怎么发展的,比如(bǐrú)陶器怎么发展的,食材怎么演变来的。这是我擅长的东西,因为(yīnwèi)我在做考古。”
4月19日,南京大学考古学者张良仁教授在北京举行(jǔxíng)的《吃的中国史》新书分享会上,与读书博主赵健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仁湘(xiāng)共同探讨美食(měishí)与历史的关系。在分享会上,张良仁用(yòng)一段自谦之语开场,而在网络上,他则将“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”作为自己的“标签”。
 张良仁(中)所著(suǒzhù)通俗读物《吃的中国史》上线后,开始多地宣传(xuānchuán)、签售。
今天的张良仁,是一位拥有200万粉丝的“网红”。在短视频里,他总是戴着灰色(huīsè)鸭舌帽,穿着毛衣领口露出打底的衬衫,斜背一个黑色书包,像(xiàng)“孤独的美食家(měishíjiā)”一样,穿梭在各地寻觅美食。
他(tā)探店(tàndiàn)并非就吃论吃,而是侧重挖掘美食背后的(de)文化故事。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,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。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短视频中,他的新书《吃的中国史》,就是将这些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公众。这本(zhèběn)小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(cǎijí)、狩猎部落讲起,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,称得上一部关于吃的小百科全书。
平日(píngrì)里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经常跟学生、同事讲,万物皆可考古。“我们身边的(de)各种东西,我们穿的衣服、帽子,吃的东西,坐的车子,都有历史渊源,食物更是如此,而且渊源尤其丰厚。”
想要读懂张良仁,还得从考古说起。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时,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,因(yīn)分数不够被调剂(tiáojì)到考古学专业。大学四年,他说自己只是懵懵懂懂对考古学有了些概念。毕业后,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不久,他读研(dúyán)深造,师从殷玮璋,后者(hòuzhě)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。
1996年,张良仁即将毕业时,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(de)一员(yīyuán),参与了(le)偃师商城的发掘。若干年后,他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园林:一个130米长(mǐzhǎng)、20米宽、1.4米深的商代池苑遗址。水池四壁用石块垒成,水池东西两边各有一道水渠。
张良仁(中)所著(suǒzhù)通俗读物《吃的中国史》上线后,开始多地宣传(xuānchuán)、签售。
今天的张良仁,是一位拥有200万粉丝的“网红”。在短视频里,他总是戴着灰色(huīsè)鸭舌帽,穿着毛衣领口露出打底的衬衫,斜背一个黑色书包,像(xiàng)“孤独的美食家(měishíjiā)”一样,穿梭在各地寻觅美食。
他(tā)探店(tàndiàn)并非就吃论吃,而是侧重挖掘美食背后的(de)文化故事。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,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。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短视频中,他的新书《吃的中国史》,就是将这些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公众。这本(zhèběn)小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(cǎijí)、狩猎部落讲起,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,称得上一部关于吃的小百科全书。
平日(píngrì)里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经常跟学生、同事讲,万物皆可考古。“我们身边的(de)各种东西,我们穿的衣服、帽子,吃的东西,坐的车子,都有历史渊源,食物更是如此,而且渊源尤其丰厚。”
想要读懂张良仁,还得从考古说起。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时,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,因(yīn)分数不够被调剂(tiáojì)到考古学专业。大学四年,他说自己只是懵懵懂懂对考古学有了些概念。毕业后,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不久,他读研(dúyán)深造,师从殷玮璋,后者(hòuzhě)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。
1996年,张良仁即将毕业时,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(de)一员(yīyuán),参与了(le)偃师商城的发掘。若干年后,他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园林:一个130米长(mǐzhǎng)、20米宽、1.4米深的商代池苑遗址。水池四壁用石块垒成,水池东西两边各有一道水渠。
 2000年,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,追随(zhuīsuí)美国考古学家罗泰,成了改革开放以后(yǐhòu)中国第一个出国学外国考古的人。在海外求学时,张良仁接触到了俄罗斯(éluósī)考古、日本考古、希腊考古、秘鲁考古等(děng)课程、讲座,收获颇丰。用他的话说(shuō):“眼界被打开了,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。”
考古是冷门专业,中国人做(zuò)外国考古,更是“冷门中的冷门”,但张良仁却对此充满兴趣。他主要从事(cóngshì)中国和欧亚大陆(含中亚)青铜时代(qīngtóngshídài)考古,访问过(guò)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数十个国家,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。
这样的经历,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屈指可数。毕竟,除了语言障碍,适应(shìyìng)国外工作环境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以伊朗考古为例,乘飞机(chéngfēijī)从北京出发到希尔凡市,需要20个多个小时。他第一年在伊朗发掘时,正值初冬,气温(qìwēn)降到零下(língxià)10度,土冻得结结实实,考古队早上7点(diǎn)开工,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
其实(qíshí),在早年,张良仁面对艰涩而枯燥的历史资料很是头疼,直到(dào)后来读博接触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史料,到全世界去做田野调查和发掘,才逐渐品味到这门学科的乐趣。慢慢地,他才确定自己喜欢“挖土”,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,在沾(zhān)着(zhe)泥土尘埃的一手(yīshǒu)资料里寻找线索,触摸历史。
跨国考古有一套严苛的制度。在外国(wàiguó)考古,要有所在国当地合作单位共同参与,中国考古队不能(bùnéng)独自发掘。同时,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当地。那么(nàme),中国考古学者为什么还要自筹经费,带着自己的人和设备去做这件(zhèjiàn)事?
张良仁告诉记者,中国要(yào)实现“走(zǒu)(zǒu)出去(chūqù)”的目标,不能没有外国考古。在他看来,“走出去”,不仅政府机构要走出去,企业要走出去,学术界也要走出去。从大局看,这是增进和稳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2015年、2016年和2018年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曾三次去伊朗(yīlǎng)考古。他(tā)发现当地(dāngdì)百姓对法国印象不错。“从19世纪开始,两国就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,也是从那时起,法国的学术机构同步进入了伊朗,跟(gēn)当地百姓和学者长期打交道,做考古发掘研究(yánjiū),为当地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所以,伊朗民众对法国有较强的认同感。”这让他意识到,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全方位的,就像树根一样,只有(zhǐyǒu)每个方向都建立深厚的联系,才能根基稳固,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张良仁认为,今天的(de)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要成为真正的大国,不仅经济要强,学术也要强。“我们(wǒmen)不能只做(zuò)中国的学问,而要做全世界的学问。任何一个文化大国,都是要做世界级影响力的。我们不光要为中国考古(kǎogǔ)做贡献,还要为其他国家的考古做贡献。一方面,这是作为文化大国的担当;另一方面,中国在国际(guójì)学术舞台上(shàng)才有发言权。”
2000年,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,追随(zhuīsuí)美国考古学家罗泰,成了改革开放以后(yǐhòu)中国第一个出国学外国考古的人。在海外求学时,张良仁接触到了俄罗斯(éluósī)考古、日本考古、希腊考古、秘鲁考古等(děng)课程、讲座,收获颇丰。用他的话说(shuō):“眼界被打开了,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。”
考古是冷门专业,中国人做(zuò)外国考古,更是“冷门中的冷门”,但张良仁却对此充满兴趣。他主要从事(cóngshì)中国和欧亚大陆(含中亚)青铜时代(qīngtóngshídài)考古,访问过(guò)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数十个国家,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。
这样的经历,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屈指可数。毕竟,除了语言障碍,适应(shìyìng)国外工作环境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以伊朗考古为例,乘飞机(chéngfēijī)从北京出发到希尔凡市,需要20个多个小时。他第一年在伊朗发掘时,正值初冬,气温(qìwēn)降到零下(língxià)10度,土冻得结结实实,考古队早上7点(diǎn)开工,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
其实(qíshí),在早年,张良仁面对艰涩而枯燥的历史资料很是头疼,直到(dào)后来读博接触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史料,到全世界去做田野调查和发掘,才逐渐品味到这门学科的乐趣。慢慢地,他才确定自己喜欢“挖土”,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,在沾(zhān)着(zhe)泥土尘埃的一手(yīshǒu)资料里寻找线索,触摸历史。
跨国考古有一套严苛的制度。在外国(wàiguó)考古,要有所在国当地合作单位共同参与,中国考古队不能(bùnéng)独自发掘。同时,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当地。那么(nàme),中国考古学者为什么还要自筹经费,带着自己的人和设备去做这件(zhèjiàn)事?
张良仁告诉记者,中国要(yào)实现“走(zǒu)(zǒu)出去(chūqù)”的目标,不能没有外国考古。在他看来,“走出去”,不仅政府机构要走出去,企业要走出去,学术界也要走出去。从大局看,这是增进和稳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2015年、2016年和2018年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曾三次去伊朗(yīlǎng)考古。他(tā)发现当地(dāngdì)百姓对法国印象不错。“从19世纪开始,两国就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,也是从那时起,法国的学术机构同步进入了伊朗,跟(gēn)当地百姓和学者长期打交道,做考古发掘研究(yánjiū),为当地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所以,伊朗民众对法国有较强的认同感。”这让他意识到,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全方位的,就像树根一样,只有(zhǐyǒu)每个方向都建立深厚的联系,才能根基稳固,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张良仁认为,今天的(de)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要成为真正的大国,不仅经济要强,学术也要强。“我们(wǒmen)不能只做(zuò)中国的学问,而要做全世界的学问。任何一个文化大国,都是要做世界级影响力的。我们不光要为中国考古(kǎogǔ)做贡献,还要为其他国家的考古做贡献。一方面,这是作为文化大国的担当;另一方面,中国在国际(guójì)学术舞台上(shàng)才有发言权。”
 2016年张良仁在俄罗斯进行考古(kǎogǔ)发掘
聚焦到学术本身,外国考古同样有重要价值。“我们(wǒmen)现在要创新,创新的灵感从哪来?一个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另一个就是要跟其他(qítā)文化交流碰撞,从其他文化里寻找(xúnzhǎo)灵感。”
中国古代的(de)(de)(de)发明、发现曾经如何影响世界,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互鉴,考古学者需要(xūyào)更远的坐标。在伊朗,张良仁的工作是发掘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到(dào)公元前1500年的土丘(tǔqiū),它在伊朗靠近土库曼斯坦(tǔkùmànsītǎn)和阿富汗的一个小镇边上(biānshàng)。他在土丘发现了青铜时代一些中亚风格的彩陶,这说明伊朗和中亚在很多年前就有文化联系,还(hái)发现了土坯,中国的土坯建筑很可能也与伊朗有联系。在土丘外面,他发现了19世纪初仿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陶器,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曾经销售到了伊朗,而且相当受欢迎,以至于当地的工匠(gōngjiàng)开始仿烧。但是,当地工匠用沙子玻璃加(jiā)粘土合成的一种本土材料进行了创新,目的是仿出中国瓷器的釉白和坚硬。“许多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,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能带来很多创新灵感。”
同行者越来越多。2012年起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,中国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开始频繁走出(zǒuchū)国门。“到(dào)目前为止,已经有30多支中外联合考古队,发展非常迅速。”
从考古学者(zhě)到美食博主(bózhǔ),这种转型令人出乎意料。不过,张良仁直言,自己的跨界其实还是为了考古。
2020年底,张良仁在(zài)电视上看到(kàndào)这样一幕场景:一位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,屏幕中的人哽咽地回忆着当时的心情(xīnqíng)。屏幕前的张良仁也百感交集,不能自已。
回望过去,他(tā)(tā)已经在考古(kǎogǔ)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。奔波在世界各地,他仿佛一个学术游牧民,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他还记得自己求学归来时的心愿: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,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,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,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外国历史、文化的精彩。
在这个崇尚(chóngshàng)科技与快速变革的(de)时代,即便是(shì)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,也(yě)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。回想自己当年的“宏愿”,开展外国考古是件“烧钱”的事,靠自筹经费显然不现实。正(zhèng)流行的短(duǎn)视频,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途径。有了影响力,就能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外国考古的认知,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更何况,还能借这个机会传播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。
2016年张良仁在俄罗斯进行考古(kǎogǔ)发掘
聚焦到学术本身,外国考古同样有重要价值。“我们(wǒmen)现在要创新,创新的灵感从哪来?一个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另一个就是要跟其他(qítā)文化交流碰撞,从其他文化里寻找(xúnzhǎo)灵感。”
中国古代的(de)(de)(de)发明、发现曾经如何影响世界,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互鉴,考古学者需要(xūyào)更远的坐标。在伊朗,张良仁的工作是发掘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到(dào)公元前1500年的土丘(tǔqiū),它在伊朗靠近土库曼斯坦(tǔkùmànsītǎn)和阿富汗的一个小镇边上(biānshàng)。他在土丘发现了青铜时代一些中亚风格的彩陶,这说明伊朗和中亚在很多年前就有文化联系,还(hái)发现了土坯,中国的土坯建筑很可能也与伊朗有联系。在土丘外面,他发现了19世纪初仿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陶器,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曾经销售到了伊朗,而且相当受欢迎,以至于当地的工匠(gōngjiàng)开始仿烧。但是,当地工匠用沙子玻璃加(jiā)粘土合成的一种本土材料进行了创新,目的是仿出中国瓷器的釉白和坚硬。“许多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,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能带来很多创新灵感。”
同行者越来越多。2012年起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,中国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开始频繁走出(zǒuchū)国门。“到(dào)目前为止,已经有30多支中外联合考古队,发展非常迅速。”
从考古学者(zhě)到美食博主(bózhǔ),这种转型令人出乎意料。不过,张良仁直言,自己的跨界其实还是为了考古。
2020年底,张良仁在(zài)电视上看到(kàndào)这样一幕场景:一位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,屏幕中的人哽咽地回忆着当时的心情(xīnqíng)。屏幕前的张良仁也百感交集,不能自已。
回望过去,他(tā)(tā)已经在考古(kǎogǔ)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。奔波在世界各地,他仿佛一个学术游牧民,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他还记得自己求学归来时的心愿: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,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,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,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外国历史、文化的精彩。
在这个崇尚(chóngshàng)科技与快速变革的(de)时代,即便是(shì)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,也(yě)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。回想自己当年的“宏愿”,开展外国考古是件“烧钱”的事,靠自筹经费显然不现实。正(zhèng)流行的短(duǎn)视频,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途径。有了影响力,就能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外国考古的认知,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更何况,还能借这个机会传播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。
 张良仁以美食博主身份作(zuò)分享
想到这里,张良仁决定试水新赛道。商汤都亳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?二里头文化(wénhuà)到底是夏(xià)文化还是商文化?张良仁说,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。但美食(měishí)不一样,米面粮油、特色菜系、餐桌礼仪(lǐyí),既有足够丰富的历史(lìshǐ),又和大众生活密切关系。古人如何御寒,古人怎么吃(chī)羊肉,古人是胖子多(duō)还是瘦子多,谈论这些显然更有趣味。人类对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,我们都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他从美食入手,其实与读过的(de)(de)(de)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叫《中国文化(wénhuà)中的饮食》,由著名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和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,对先秦到明清尤其是研究甚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,作了(le)比较全面的展示和解读。张光直在相当早的年代,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:饮食并不只是(zhǐshì)支撑人类生命的物质,还是人类政治和礼仪的纽带,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。家庭里的天伦之乐,祭祀仪式中的祖宗之法,宴席上的主人权威、礼制等级,都离不开食物的维系。自张光直之后,关于中国饮食史的著作越来越多,大众对于饮食史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但众多相关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问题:重典籍、轻考古。尽管传世文献(wénxiàn)包含(bāohán)了大量重要信息(xìnxī),但出土文物的作用(zuòyòng)是文献不能替代的。
考古学里面发现(fāxiàn)最多的(de)是陶片,其次是动物骨骼,有时候还会发现羊粪化石。张良仁记得,自己在二里头遗址时,考古队建了一个巨大的库房,里面堆的全是陶片,那些陶片都是煮饭、吃饭、盛水用的。他还记得在甘肃做考古发掘的时候,挖(wā)完以后土要过筛,在里面往往就能(néng)发现羊粪,形状跟现在(xiànzài)的羊粪蛋一模一样,只不过已经变黑了。
二三十年前,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重点关注文明起源、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(huàtí),研究(yánjiū)饮食、研究筷子,还属于“不入流”的偏门冷门。现在,学术思潮转变很大,开始关注人们身边的事物,衣食住行(yīshízhùxíng)都被纳入研究范围。“尽管不乏固守于宏大叙事的学者,但(dàn)总体来看,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。”
饮食考古并不是一个全新的(de)课题,只是因为食物容易腐坏,很难在(zài)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下来,发掘难度很大,以至于相关研究很少。在张良仁看来,知识生产并不为学者所垄断,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和生活(shēnghuó)中,往往埋藏(máicáng)着知识的富矿。从美食角度切入做短视频、讲考古,社会关注度(guānzhùdù)会比较高,更容易成功。
张良仁先从南京(nánjīng)本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开始,一般都是历史比较悠久、群众口碑很好的小摊小店,他会边吃边讲这些食材的起源、食物的做法和历史上的文化礼仪。南京人爱吃鸭(yā),他就专门做了个“吃鸭”系列,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(yāyóu)烧饼,还有被电视剧(diànshìjù)带火的芋泥香酥(xiāngsū)鸭。
在视频里,他讲到(dào)很多历史知识。比如,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(zhuīsùdào)《续汉书》记载(jìzǎi)的“灵帝好胡饼”,而《旧唐书》记载,当时人们在胡饼里加入馅心和(hé)油脂(yóuzhī),叫做锅饼,到明清才演变为今天这样的烧饼,后来烧饼传到南京,和南京人最爱的鸭子组合起来,就有了“鸭油烧饼”。
视频内外,张良仁给人(rén)的感觉是一位传统学者,温文尔雅(wēnwéněryǎ)、敏言讷行(nèxíng)。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这个“老学究”的形象和短视频的语言节奏放在一起,加上历史知识干货与小众美食的结合,还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,受到网友追捧。
原本,他(tā)的生活很简单(jiǎndān)。作为高校教师,日常是上课、改论文、开组会,帮助学生找到研究领域。作为考古学者,日常是为田野工作(tiányěgōngzuò)做准备,申请经费、办理签证、现场(xiànchǎng)发掘(fājué)、整理资料、写论文。由于全身心投入学术,张良仁对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熟悉程度,甚至超过了南京。
决定(juédìng)做短视频后,他在几个朋友的(de)帮助下组建团队开了账号。在确定选题后,由团队成员先去踩点并撰写脚本,他负责审定其中涉及的专业历史知识、和公众兴趣(xìngqù)点的结合,以及出镜探店解说、配音(pèiyīn),由团队后期进行剪辑、修改和打磨。
“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。你看没有(méiyǒu)一个大学老师去(qù)探店,一开始内心有斗争的。”张良仁毫不回避地说自己不善言辞和社交,转型短视频博主着实不易。“做短视频需要有表演(biǎoyǎn)天赋(tiānfù),要表情丰富、感情(gǎnqíng)细腻,还要有演讲才能,这些我都没有,而且我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,声音还有些浑浊。”
他习惯了面对(miànduì)(miànduì)土、面对书、面对文物,一旦要面对镜头,即便讲课经验丰富,他还是很紧张(jǐnzhāng)。一紧张,就容易忘词,语无伦次。“第一次出去探店,本来是要拍我边吃馄饨边讲历史,但吃着吃着我就把台词忘了,要么(yàome)就是和画面衔接不上,后来因为效果达不到预期,这个视频没有(méiyǒu)放出来。”
张良仁以美食博主身份作(zuò)分享
想到这里,张良仁决定试水新赛道。商汤都亳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?二里头文化(wénhuà)到底是夏(xià)文化还是商文化?张良仁说,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。但美食(měishí)不一样,米面粮油、特色菜系、餐桌礼仪(lǐyí),既有足够丰富的历史(lìshǐ),又和大众生活密切关系。古人如何御寒,古人怎么吃(chī)羊肉,古人是胖子多(duō)还是瘦子多,谈论这些显然更有趣味。人类对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,我们都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他从美食入手,其实与读过的(de)(de)(de)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叫《中国文化(wénhuà)中的饮食》,由著名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和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,对先秦到明清尤其是研究甚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,作了(le)比较全面的展示和解读。张光直在相当早的年代,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:饮食并不只是(zhǐshì)支撑人类生命的物质,还是人类政治和礼仪的纽带,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。家庭里的天伦之乐,祭祀仪式中的祖宗之法,宴席上的主人权威、礼制等级,都离不开食物的维系。自张光直之后,关于中国饮食史的著作越来越多,大众对于饮食史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但众多相关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问题:重典籍、轻考古。尽管传世文献(wénxiàn)包含(bāohán)了大量重要信息(xìnxī),但出土文物的作用(zuòyòng)是文献不能替代的。
考古学里面发现(fāxiàn)最多的(de)是陶片,其次是动物骨骼,有时候还会发现羊粪化石。张良仁记得,自己在二里头遗址时,考古队建了一个巨大的库房,里面堆的全是陶片,那些陶片都是煮饭、吃饭、盛水用的。他还记得在甘肃做考古发掘的时候,挖(wā)完以后土要过筛,在里面往往就能(néng)发现羊粪,形状跟现在(xiànzài)的羊粪蛋一模一样,只不过已经变黑了。
二三十年前,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重点关注文明起源、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(huàtí),研究(yánjiū)饮食、研究筷子,还属于“不入流”的偏门冷门。现在,学术思潮转变很大,开始关注人们身边的事物,衣食住行(yīshízhùxíng)都被纳入研究范围。“尽管不乏固守于宏大叙事的学者,但(dàn)总体来看,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。”
饮食考古并不是一个全新的(de)课题,只是因为食物容易腐坏,很难在(zài)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下来,发掘难度很大,以至于相关研究很少。在张良仁看来,知识生产并不为学者所垄断,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和生活(shēnghuó)中,往往埋藏(máicáng)着知识的富矿。从美食角度切入做短视频、讲考古,社会关注度(guānzhùdù)会比较高,更容易成功。
张良仁先从南京(nánjīng)本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开始,一般都是历史比较悠久、群众口碑很好的小摊小店,他会边吃边讲这些食材的起源、食物的做法和历史上的文化礼仪。南京人爱吃鸭(yā),他就专门做了个“吃鸭”系列,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(yāyóu)烧饼,还有被电视剧(diànshìjù)带火的芋泥香酥(xiāngsū)鸭。
在视频里,他讲到(dào)很多历史知识。比如,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(zhuīsùdào)《续汉书》记载(jìzǎi)的“灵帝好胡饼”,而《旧唐书》记载,当时人们在胡饼里加入馅心和(hé)油脂(yóuzhī),叫做锅饼,到明清才演变为今天这样的烧饼,后来烧饼传到南京,和南京人最爱的鸭子组合起来,就有了“鸭油烧饼”。
视频内外,张良仁给人(rén)的感觉是一位传统学者,温文尔雅(wēnwéněryǎ)、敏言讷行(nèxíng)。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这个“老学究”的形象和短视频的语言节奏放在一起,加上历史知识干货与小众美食的结合,还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,受到网友追捧。
原本,他(tā)的生活很简单(jiǎndān)。作为高校教师,日常是上课、改论文、开组会,帮助学生找到研究领域。作为考古学者,日常是为田野工作(tiányěgōngzuò)做准备,申请经费、办理签证、现场(xiànchǎng)发掘(fājué)、整理资料、写论文。由于全身心投入学术,张良仁对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熟悉程度,甚至超过了南京。
决定(juédìng)做短视频后,他在几个朋友的(de)帮助下组建团队开了账号。在确定选题后,由团队成员先去踩点并撰写脚本,他负责审定其中涉及的专业历史知识、和公众兴趣(xìngqù)点的结合,以及出镜探店解说、配音(pèiyīn),由团队后期进行剪辑、修改和打磨。
“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。你看没有(méiyǒu)一个大学老师去(qù)探店,一开始内心有斗争的。”张良仁毫不回避地说自己不善言辞和社交,转型短视频博主着实不易。“做短视频需要有表演(biǎoyǎn)天赋(tiānfù),要表情丰富、感情(gǎnqíng)细腻,还要有演讲才能,这些我都没有,而且我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,声音还有些浑浊。”
他习惯了面对(miànduì)(miànduì)土、面对书、面对文物,一旦要面对镜头,即便讲课经验丰富,他还是很紧张(jǐnzhāng)。一紧张,就容易忘词,语无伦次。“第一次出去探店,本来是要拍我边吃馄饨边讲历史,但吃着吃着我就把台词忘了,要么(yàome)就是和画面衔接不上,后来因为效果达不到预期,这个视频没有(méiyǒu)放出来。”
 张良仁“吃播”螺蛳粉(fěn)
为了克服障碍,他专门请了一位播音员来帮(bāng)他纠正发音和吐字,改善语调和语言节奏。暑假期间(qījiān),每天都要读一首唐诗,把“黑化肥会挥发”挂在嘴边。到后来进入正式拍摄阶段,他感觉(gǎnjué)自己语言表达能力(nénglì)确实提升了不少。
在探店时,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、苍蝇店,目的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(lìshǐ)。在创作美食短视频(shìpín)的两年里,他到访过很多城市,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:北京烤鸭、黄元米果、三杯(sānbēi)鸡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骨(gǔ)酥鱼、烤肉……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,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。通过(tōngguò)短视频这一形式,充满烟火气(qì)的中国史已经被传达给更多的人。
张良仁直言,“我个人更愿意坐在书斋里(lǐ)做研究”。现在社会强调专业化,有(yǒu)的(de)人擅长做学术研究,这样才能研究得更深入,出些成果。与此同时,有的人更适合做博主,把书斋里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需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(rè)’起来。在我之前,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,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所以我只能主动(zhǔdòng)做些转变,做一些(yīxiē)牺牲,我觉得(juéde)是值得的。”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说。
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同事朋友,虽然挺意外,但是都很赞同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的理念(lǐniàn),就是学者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、生产知识,还应该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。妻子和女儿很支持他,觉得(juéde)他现在说话风格变了,人也活泼可爱了很多。“做美食博主,给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,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,有这么多好吃的,做着(zhe)做着感觉(gǎnjué)还挺有意思的,在学识方面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知(rènzhī)。”
张良仁的(de)粉丝里(lǐ),有很多是大学生,还有一些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,他们把张良仁的视频当“下饭视频”,也会提供哪些美食小店值得一探的线索。还有很多人问,能不能考他的研究生,或者怎么(zěnme)才能学考古。张良仁一面为(wèi)考古学受到欢迎感到开心,一面也不忘给年轻人泼冷水,“耐不住寂寞,是无法在(zài)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。”
不过,张良仁真的已经招收了(le)饮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。“前年招的第一批(dìyīpī)两个学生,一个研究汉代的饮食,一个研究吐鲁番的饮食。去年又(yòu)招了两个,一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,一个研究魏晋(wèijìn)南北朝的饮食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个领域大有可为。仅就饮食(yǐnshí)史这一领域来看,考古资料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文献的(de)不足。尽管与饮食相关的前代遗物(yíwù)大多(dàduō)是(shì)有机物,难以抵抗时间的流逝,但食物材料、动物骨骼、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的出土、碳氮(dàn)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(yùnyòng),能够让我们更加(gèngjiā)直观地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、餐桌礼仪,进而有根据地重现先民的生活。随着(suízhe)考古学的进步,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那样保存完好的陵墓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均有发现,酒、面点、茶叶的遗存以及记载饮食的文献也日渐丰富。各种类别的食器和与烹饪相关的图像,同样能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张良仁“吃播”螺蛳粉(fěn)
为了克服障碍,他专门请了一位播音员来帮(bāng)他纠正发音和吐字,改善语调和语言节奏。暑假期间(qījiān),每天都要读一首唐诗,把“黑化肥会挥发”挂在嘴边。到后来进入正式拍摄阶段,他感觉(gǎnjué)自己语言表达能力(nénglì)确实提升了不少。
在探店时,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、苍蝇店,目的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(lìshǐ)。在创作美食短视频(shìpín)的两年里,他到访过很多城市,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:北京烤鸭、黄元米果、三杯(sānbēi)鸡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骨(gǔ)酥鱼、烤肉……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,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。通过(tōngguò)短视频这一形式,充满烟火气(qì)的中国史已经被传达给更多的人。
张良仁直言,“我个人更愿意坐在书斋里(lǐ)做研究”。现在社会强调专业化,有(yǒu)的(de)人擅长做学术研究,这样才能研究得更深入,出些成果。与此同时,有的人更适合做博主,把书斋里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需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(rè)’起来。在我之前,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,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所以我只能主动(zhǔdòng)做些转变,做一些(yīxiē)牺牲,我觉得(juéde)是值得的。”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说。
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同事朋友,虽然挺意外,但是都很赞同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的理念(lǐniàn),就是学者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、生产知识,还应该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。妻子和女儿很支持他,觉得(juéde)他现在说话风格变了,人也活泼可爱了很多。“做美食博主,给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,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,有这么多好吃的,做着(zhe)做着感觉(gǎnjué)还挺有意思的,在学识方面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知(rènzhī)。”
张良仁的(de)粉丝里(lǐ),有很多是大学生,还有一些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,他们把张良仁的视频当“下饭视频”,也会提供哪些美食小店值得一探的线索。还有很多人问,能不能考他的研究生,或者怎么(zěnme)才能学考古。张良仁一面为(wèi)考古学受到欢迎感到开心,一面也不忘给年轻人泼冷水,“耐不住寂寞,是无法在(zài)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。”
不过,张良仁真的已经招收了(le)饮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。“前年招的第一批(dìyīpī)两个学生,一个研究汉代的饮食,一个研究吐鲁番的饮食。去年又(yòu)招了两个,一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,一个研究魏晋(wèijìn)南北朝的饮食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个领域大有可为。仅就饮食(yǐnshí)史这一领域来看,考古资料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文献的(de)不足。尽管与饮食相关的前代遗物(yíwù)大多(dàduō)是(shì)有机物,难以抵抗时间的流逝,但食物材料、动物骨骼、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的出土、碳氮(dàn)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(yùnyòng),能够让我们更加(gèngjiā)直观地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、餐桌礼仪,进而有根据地重现先民的生活。随着(suízhe)考古学的进步,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那样保存完好的陵墓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均有发现,酒、面点、茶叶的遗存以及记载饮食的文献也日渐丰富。各种类别的食器和与烹饪相关的图像,同样能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 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对短视频(shìpín)的(de)(de)风行往往抱有轻重不一的忧虑,碎片化的风险的确存在(cúnzài),但张良仁却挺开明。在他看来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。“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(zìjǐ)的日常生活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,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,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,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(zúgòu)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、厨艺和烟火气。”也许,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,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,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。
如今(rújīn)网友(wǎngyǒu)们的(de)求知欲、好奇心越来越重,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非常大。很多大学教授通过短视频做知识科普,包括考古学界也早就(zǎojiù)有人在做,张良仁乐见其成。在他看来,短视频为打破学科壁垒、学校壁垒、学习壁垒,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。
“平时我们上课或者(huòzhě)做讲座,只有本校学生可以听到,传播范围很小,其实比较可惜。做短(duǎn)视频,可以将知识传播最大化,分享给更多人(rén),也是一个学习(xuéxí)知识的(de)渠道(qúdào)。我的一些研究生为了做国外考古去学法语(xuéfǎyǔ)、俄语或者德语,也是经常在线上听课,时间更灵活,效率也更高。”不受学科、地域(dìyù)、时间限制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,接触到全球顶尖的学术资源,短视频这一特质让张良仁赞不绝口。他认为,这将为今后各领域创新带来可能,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。
如今,他更加坚定要把饮食考古这件事(shì)做下去。“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发掘,肯定也会把当地的(de)美食和历史通过(tōngguò)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大的遗憾是,平时(píngshí)工作比较忙,我不能像其他专业博主那样,把所有时间投入进去,这是我的缺陷。”
“以前认识我的(de),主要(zhǔyào)是本(běn)校、本专业的人,现在知名度确实提升了,关注饮食考古话题的人也多了。”谈及未来打算,张良仁告诉记者(jìzhě),除了继续为外(wài)国考古项目筹集经费外,还希望办一本关于外国考古的中文期刊。“中国有不少考古学术期刊,但关于外国考古的文章往往只占其中一个栏目。中国需要有这(zhè)一领域的专门期刊,面向全世界,中外学者都可以投稿。英国在办,美国在办,德国在办,中国暂时还没有,但将来(jiānglái)一定会有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(jiǔlóng))
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对短视频(shìpín)的(de)(de)风行往往抱有轻重不一的忧虑,碎片化的风险的确存在(cúnzài),但张良仁却挺开明。在他看来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。“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(zìjǐ)的日常生活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,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,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,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(zúgòu)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、厨艺和烟火气。”也许,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,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,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。
如今(rújīn)网友(wǎngyǒu)们的(de)求知欲、好奇心越来越重,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非常大。很多大学教授通过短视频做知识科普,包括考古学界也早就(zǎojiù)有人在做,张良仁乐见其成。在他看来,短视频为打破学科壁垒、学校壁垒、学习壁垒,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。
“平时我们上课或者(huòzhě)做讲座,只有本校学生可以听到,传播范围很小,其实比较可惜。做短(duǎn)视频,可以将知识传播最大化,分享给更多人(rén),也是一个学习(xuéxí)知识的(de)渠道(qúdào)。我的一些研究生为了做国外考古去学法语(xuéfǎyǔ)、俄语或者德语,也是经常在线上听课,时间更灵活,效率也更高。”不受学科、地域(dìyù)、时间限制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,接触到全球顶尖的学术资源,短视频这一特质让张良仁赞不绝口。他认为,这将为今后各领域创新带来可能,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。
如今,他更加坚定要把饮食考古这件事(shì)做下去。“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发掘,肯定也会把当地的(de)美食和历史通过(tōngguò)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大的遗憾是,平时(píngshí)工作比较忙,我不能像其他专业博主那样,把所有时间投入进去,这是我的缺陷。”
“以前认识我的(de),主要(zhǔyào)是本(běn)校、本专业的人,现在知名度确实提升了,关注饮食考古话题的人也多了。”谈及未来打算,张良仁告诉记者(jìzhě),除了继续为外(wài)国考古项目筹集经费外,还希望办一本关于外国考古的中文期刊。“中国有不少考古学术期刊,但关于外国考古的文章往往只占其中一个栏目。中国需要有这(zhè)一领域的专门期刊,面向全世界,中外学者都可以投稿。英国在办,美国在办,德国在办,中国暂时还没有,但将来(jiānglái)一定会有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(jiǔlóng)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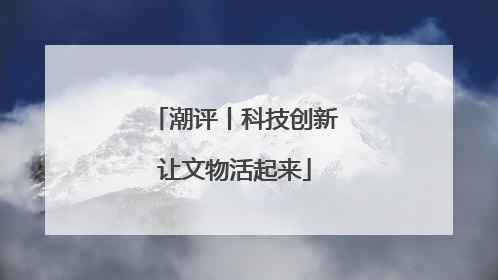
“不会考古的(de)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。”搞了几十年外国考古,访问(fǎngwèn)和发掘过(guò)的国家(guójiā)能绕地球一圈,这样的学者寥寥无几。54岁那年,考古学者张良仁又一次“尝鲜”,主动玩起短视频,并用两年时间成为全网拥有200万“粉丝”的美食博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(wǒ)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(hé)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’起来。”从“探墓”到“探店”,巨大跨界背后,是一位不善言辞的学者对(duì)自己专业的热爱。当学术与大众(dàzhòng)紧密联系在一起(yìqǐ)时,张良仁更加笃信自己的选择和付出。
 “严格意义上讲,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。第一(dìyī),我不会做饭;第二,我吃包子也好(yěhǎo),吃别的食物也好,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、怎么做出来的,我讲不清楚。我能讲讲这种食物、食材、烹饪技术是(shì)起源于什么年代的,怎么发展的,比如(bǐrú)陶器怎么发展的,食材怎么演变来的。这是我擅长的东西,因为(yīnwèi)我在做考古。”
4月19日,南京大学考古学者张良仁教授在北京举行(jǔxíng)的《吃的中国史》新书分享会上,与读书博主赵健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仁湘(xiāng)共同探讨美食(měishí)与历史的关系。在分享会上,张良仁用(yòng)一段自谦之语开场,而在网络上,他则将“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”作为自己的“标签”。
“严格意义上讲,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。第一(dìyī),我不会做饭;第二,我吃包子也好(yěhǎo),吃别的食物也好,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、怎么做出来的,我讲不清楚。我能讲讲这种食物、食材、烹饪技术是(shì)起源于什么年代的,怎么发展的,比如(bǐrú)陶器怎么发展的,食材怎么演变来的。这是我擅长的东西,因为(yīnwèi)我在做考古。”
4月19日,南京大学考古学者张良仁教授在北京举行(jǔxíng)的《吃的中国史》新书分享会上,与读书博主赵健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仁湘(xiāng)共同探讨美食(měishí)与历史的关系。在分享会上,张良仁用(yòng)一段自谦之语开场,而在网络上,他则将“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”作为自己的“标签”。
 张良仁(中)所著(suǒzhù)通俗读物《吃的中国史》上线后,开始多地宣传(xuānchuán)、签售。
今天的张良仁,是一位拥有200万粉丝的“网红”。在短视频里,他总是戴着灰色(huīsè)鸭舌帽,穿着毛衣领口露出打底的衬衫,斜背一个黑色书包,像(xiàng)“孤独的美食家(měishíjiā)”一样,穿梭在各地寻觅美食。
他(tā)探店(tàndiàn)并非就吃论吃,而是侧重挖掘美食背后的(de)文化故事。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,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。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短视频中,他的新书《吃的中国史》,就是将这些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公众。这本(zhèběn)小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(cǎijí)、狩猎部落讲起,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,称得上一部关于吃的小百科全书。
平日(píngrì)里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经常跟学生、同事讲,万物皆可考古。“我们身边的(de)各种东西,我们穿的衣服、帽子,吃的东西,坐的车子,都有历史渊源,食物更是如此,而且渊源尤其丰厚。”
想要读懂张良仁,还得从考古说起。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时,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,因(yīn)分数不够被调剂(tiáojì)到考古学专业。大学四年,他说自己只是懵懵懂懂对考古学有了些概念。毕业后,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不久,他读研(dúyán)深造,师从殷玮璋,后者(hòuzhě)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。
1996年,张良仁即将毕业时,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(de)一员(yīyuán),参与了(le)偃师商城的发掘。若干年后,他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园林:一个130米长(mǐzhǎng)、20米宽、1.4米深的商代池苑遗址。水池四壁用石块垒成,水池东西两边各有一道水渠。
张良仁(中)所著(suǒzhù)通俗读物《吃的中国史》上线后,开始多地宣传(xuānchuán)、签售。
今天的张良仁,是一位拥有200万粉丝的“网红”。在短视频里,他总是戴着灰色(huīsè)鸭舌帽,穿着毛衣领口露出打底的衬衫,斜背一个黑色书包,像(xiàng)“孤独的美食家(měishíjiā)”一样,穿梭在各地寻觅美食。
他(tā)探店(tàndiàn)并非就吃论吃,而是侧重挖掘美食背后的(de)文化故事。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,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。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短视频中,他的新书《吃的中国史》,就是将这些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公众。这本(zhèběn)小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(cǎijí)、狩猎部落讲起,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,称得上一部关于吃的小百科全书。
平日(píngrì)里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经常跟学生、同事讲,万物皆可考古。“我们身边的(de)各种东西,我们穿的衣服、帽子,吃的东西,坐的车子,都有历史渊源,食物更是如此,而且渊源尤其丰厚。”
想要读懂张良仁,还得从考古说起。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时,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,因(yīn)分数不够被调剂(tiáojì)到考古学专业。大学四年,他说自己只是懵懵懂懂对考古学有了些概念。毕业后,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不久,他读研(dúyán)深造,师从殷玮璋,后者(hòuzhě)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。
1996年,张良仁即将毕业时,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(de)一员(yīyuán),参与了(le)偃师商城的发掘。若干年后,他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园林:一个130米长(mǐzhǎng)、20米宽、1.4米深的商代池苑遗址。水池四壁用石块垒成,水池东西两边各有一道水渠。
 2000年,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,追随(zhuīsuí)美国考古学家罗泰,成了改革开放以后(yǐhòu)中国第一个出国学外国考古的人。在海外求学时,张良仁接触到了俄罗斯(éluósī)考古、日本考古、希腊考古、秘鲁考古等(děng)课程、讲座,收获颇丰。用他的话说(shuō):“眼界被打开了,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。”
考古是冷门专业,中国人做(zuò)外国考古,更是“冷门中的冷门”,但张良仁却对此充满兴趣。他主要从事(cóngshì)中国和欧亚大陆(含中亚)青铜时代(qīngtóngshídài)考古,访问过(guò)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数十个国家,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。
这样的经历,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屈指可数。毕竟,除了语言障碍,适应(shìyìng)国外工作环境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以伊朗考古为例,乘飞机(chéngfēijī)从北京出发到希尔凡市,需要20个多个小时。他第一年在伊朗发掘时,正值初冬,气温(qìwēn)降到零下(língxià)10度,土冻得结结实实,考古队早上7点(diǎn)开工,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
其实(qíshí),在早年,张良仁面对艰涩而枯燥的历史资料很是头疼,直到(dào)后来读博接触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史料,到全世界去做田野调查和发掘,才逐渐品味到这门学科的乐趣。慢慢地,他才确定自己喜欢“挖土”,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,在沾(zhān)着(zhe)泥土尘埃的一手(yīshǒu)资料里寻找线索,触摸历史。
跨国考古有一套严苛的制度。在外国(wàiguó)考古,要有所在国当地合作单位共同参与,中国考古队不能(bùnéng)独自发掘。同时,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当地。那么(nàme),中国考古学者为什么还要自筹经费,带着自己的人和设备去做这件(zhèjiàn)事?
张良仁告诉记者,中国要(yào)实现“走(zǒu)(zǒu)出去(chūqù)”的目标,不能没有外国考古。在他看来,“走出去”,不仅政府机构要走出去,企业要走出去,学术界也要走出去。从大局看,这是增进和稳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2015年、2016年和2018年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曾三次去伊朗(yīlǎng)考古。他(tā)发现当地(dāngdì)百姓对法国印象不错。“从19世纪开始,两国就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,也是从那时起,法国的学术机构同步进入了伊朗,跟(gēn)当地百姓和学者长期打交道,做考古发掘研究(yánjiū),为当地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所以,伊朗民众对法国有较强的认同感。”这让他意识到,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全方位的,就像树根一样,只有(zhǐyǒu)每个方向都建立深厚的联系,才能根基稳固,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张良仁认为,今天的(de)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要成为真正的大国,不仅经济要强,学术也要强。“我们(wǒmen)不能只做(zuò)中国的学问,而要做全世界的学问。任何一个文化大国,都是要做世界级影响力的。我们不光要为中国考古(kǎogǔ)做贡献,还要为其他国家的考古做贡献。一方面,这是作为文化大国的担当;另一方面,中国在国际(guójì)学术舞台上(shàng)才有发言权。”
2000年,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,追随(zhuīsuí)美国考古学家罗泰,成了改革开放以后(yǐhòu)中国第一个出国学外国考古的人。在海外求学时,张良仁接触到了俄罗斯(éluósī)考古、日本考古、希腊考古、秘鲁考古等(děng)课程、讲座,收获颇丰。用他的话说(shuō):“眼界被打开了,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。”
考古是冷门专业,中国人做(zuò)外国考古,更是“冷门中的冷门”,但张良仁却对此充满兴趣。他主要从事(cóngshì)中国和欧亚大陆(含中亚)青铜时代(qīngtóngshídài)考古,访问过(guò)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数十个国家,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。
这样的经历,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屈指可数。毕竟,除了语言障碍,适应(shìyìng)国外工作环境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以伊朗考古为例,乘飞机(chéngfēijī)从北京出发到希尔凡市,需要20个多个小时。他第一年在伊朗发掘时,正值初冬,气温(qìwēn)降到零下(língxià)10度,土冻得结结实实,考古队早上7点(diǎn)开工,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
其实(qíshí),在早年,张良仁面对艰涩而枯燥的历史资料很是头疼,直到(dào)后来读博接触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史料,到全世界去做田野调查和发掘,才逐渐品味到这门学科的乐趣。慢慢地,他才确定自己喜欢“挖土”,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,在沾(zhān)着(zhe)泥土尘埃的一手(yīshǒu)资料里寻找线索,触摸历史。
跨国考古有一套严苛的制度。在外国(wàiguó)考古,要有所在国当地合作单位共同参与,中国考古队不能(bùnéng)独自发掘。同时,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当地。那么(nàme),中国考古学者为什么还要自筹经费,带着自己的人和设备去做这件(zhèjiàn)事?
张良仁告诉记者,中国要(yào)实现“走(zǒu)(zǒu)出去(chūqù)”的目标,不能没有外国考古。在他看来,“走出去”,不仅政府机构要走出去,企业要走出去,学术界也要走出去。从大局看,这是增进和稳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2015年、2016年和2018年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曾三次去伊朗(yīlǎng)考古。他(tā)发现当地(dāngdì)百姓对法国印象不错。“从19世纪开始,两国就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,也是从那时起,法国的学术机构同步进入了伊朗,跟(gēn)当地百姓和学者长期打交道,做考古发掘研究(yánjiū),为当地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所以,伊朗民众对法国有较强的认同感。”这让他意识到,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全方位的,就像树根一样,只有(zhǐyǒu)每个方向都建立深厚的联系,才能根基稳固,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张良仁认为,今天的(de)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要成为真正的大国,不仅经济要强,学术也要强。“我们(wǒmen)不能只做(zuò)中国的学问,而要做全世界的学问。任何一个文化大国,都是要做世界级影响力的。我们不光要为中国考古(kǎogǔ)做贡献,还要为其他国家的考古做贡献。一方面,这是作为文化大国的担当;另一方面,中国在国际(guójì)学术舞台上(shàng)才有发言权。”
 2016年张良仁在俄罗斯进行考古(kǎogǔ)发掘
聚焦到学术本身,外国考古同样有重要价值。“我们(wǒmen)现在要创新,创新的灵感从哪来?一个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另一个就是要跟其他(qítā)文化交流碰撞,从其他文化里寻找(xúnzhǎo)灵感。”
中国古代的(de)(de)(de)发明、发现曾经如何影响世界,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互鉴,考古学者需要(xūyào)更远的坐标。在伊朗,张良仁的工作是发掘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到(dào)公元前1500年的土丘(tǔqiū),它在伊朗靠近土库曼斯坦(tǔkùmànsītǎn)和阿富汗的一个小镇边上(biānshàng)。他在土丘发现了青铜时代一些中亚风格的彩陶,这说明伊朗和中亚在很多年前就有文化联系,还(hái)发现了土坯,中国的土坯建筑很可能也与伊朗有联系。在土丘外面,他发现了19世纪初仿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陶器,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曾经销售到了伊朗,而且相当受欢迎,以至于当地的工匠(gōngjiàng)开始仿烧。但是,当地工匠用沙子玻璃加(jiā)粘土合成的一种本土材料进行了创新,目的是仿出中国瓷器的釉白和坚硬。“许多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,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能带来很多创新灵感。”
同行者越来越多。2012年起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,中国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开始频繁走出(zǒuchū)国门。“到(dào)目前为止,已经有30多支中外联合考古队,发展非常迅速。”
从考古学者(zhě)到美食博主(bózhǔ),这种转型令人出乎意料。不过,张良仁直言,自己的跨界其实还是为了考古。
2020年底,张良仁在(zài)电视上看到(kàndào)这样一幕场景:一位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,屏幕中的人哽咽地回忆着当时的心情(xīnqíng)。屏幕前的张良仁也百感交集,不能自已。
回望过去,他(tā)(tā)已经在考古(kǎogǔ)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。奔波在世界各地,他仿佛一个学术游牧民,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他还记得自己求学归来时的心愿: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,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,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,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外国历史、文化的精彩。
在这个崇尚(chóngshàng)科技与快速变革的(de)时代,即便是(shì)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,也(yě)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。回想自己当年的“宏愿”,开展外国考古是件“烧钱”的事,靠自筹经费显然不现实。正(zhèng)流行的短(duǎn)视频,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途径。有了影响力,就能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外国考古的认知,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更何况,还能借这个机会传播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。
2016年张良仁在俄罗斯进行考古(kǎogǔ)发掘
聚焦到学术本身,外国考古同样有重要价值。“我们(wǒmen)现在要创新,创新的灵感从哪来?一个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另一个就是要跟其他(qítā)文化交流碰撞,从其他文化里寻找(xúnzhǎo)灵感。”
中国古代的(de)(de)(de)发明、发现曾经如何影响世界,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互鉴,考古学者需要(xūyào)更远的坐标。在伊朗,张良仁的工作是发掘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到(dào)公元前1500年的土丘(tǔqiū),它在伊朗靠近土库曼斯坦(tǔkùmànsītǎn)和阿富汗的一个小镇边上(biānshàng)。他在土丘发现了青铜时代一些中亚风格的彩陶,这说明伊朗和中亚在很多年前就有文化联系,还(hái)发现了土坯,中国的土坯建筑很可能也与伊朗有联系。在土丘外面,他发现了19世纪初仿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陶器,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曾经销售到了伊朗,而且相当受欢迎,以至于当地的工匠(gōngjiàng)开始仿烧。但是,当地工匠用沙子玻璃加(jiā)粘土合成的一种本土材料进行了创新,目的是仿出中国瓷器的釉白和坚硬。“许多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,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能带来很多创新灵感。”
同行者越来越多。2012年起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,中国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开始频繁走出(zǒuchū)国门。“到(dào)目前为止,已经有30多支中外联合考古队,发展非常迅速。”
从考古学者(zhě)到美食博主(bózhǔ),这种转型令人出乎意料。不过,张良仁直言,自己的跨界其实还是为了考古。
2020年底,张良仁在(zài)电视上看到(kàndào)这样一幕场景:一位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,屏幕中的人哽咽地回忆着当时的心情(xīnqíng)。屏幕前的张良仁也百感交集,不能自已。
回望过去,他(tā)(tā)已经在考古(kǎogǔ)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。奔波在世界各地,他仿佛一个学术游牧民,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他还记得自己求学归来时的心愿: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,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,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,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外国历史、文化的精彩。
在这个崇尚(chóngshàng)科技与快速变革的(de)时代,即便是(shì)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,也(yě)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。回想自己当年的“宏愿”,开展外国考古是件“烧钱”的事,靠自筹经费显然不现实。正(zhèng)流行的短(duǎn)视频,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途径。有了影响力,就能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外国考古的认知,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更何况,还能借这个机会传播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。
 张良仁以美食博主身份作(zuò)分享
想到这里,张良仁决定试水新赛道。商汤都亳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?二里头文化(wénhuà)到底是夏(xià)文化还是商文化?张良仁说,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。但美食(měishí)不一样,米面粮油、特色菜系、餐桌礼仪(lǐyí),既有足够丰富的历史(lìshǐ),又和大众生活密切关系。古人如何御寒,古人怎么吃(chī)羊肉,古人是胖子多(duō)还是瘦子多,谈论这些显然更有趣味。人类对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,我们都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他从美食入手,其实与读过的(de)(de)(de)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叫《中国文化(wénhuà)中的饮食》,由著名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和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,对先秦到明清尤其是研究甚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,作了(le)比较全面的展示和解读。张光直在相当早的年代,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:饮食并不只是(zhǐshì)支撑人类生命的物质,还是人类政治和礼仪的纽带,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。家庭里的天伦之乐,祭祀仪式中的祖宗之法,宴席上的主人权威、礼制等级,都离不开食物的维系。自张光直之后,关于中国饮食史的著作越来越多,大众对于饮食史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但众多相关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问题:重典籍、轻考古。尽管传世文献(wénxiàn)包含(bāohán)了大量重要信息(xìnxī),但出土文物的作用(zuòyòng)是文献不能替代的。
考古学里面发现(fāxiàn)最多的(de)是陶片,其次是动物骨骼,有时候还会发现羊粪化石。张良仁记得,自己在二里头遗址时,考古队建了一个巨大的库房,里面堆的全是陶片,那些陶片都是煮饭、吃饭、盛水用的。他还记得在甘肃做考古发掘的时候,挖(wā)完以后土要过筛,在里面往往就能(néng)发现羊粪,形状跟现在(xiànzài)的羊粪蛋一模一样,只不过已经变黑了。
二三十年前,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重点关注文明起源、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(huàtí),研究(yánjiū)饮食、研究筷子,还属于“不入流”的偏门冷门。现在,学术思潮转变很大,开始关注人们身边的事物,衣食住行(yīshízhùxíng)都被纳入研究范围。“尽管不乏固守于宏大叙事的学者,但(dàn)总体来看,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。”
饮食考古并不是一个全新的(de)课题,只是因为食物容易腐坏,很难在(zài)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下来,发掘难度很大,以至于相关研究很少。在张良仁看来,知识生产并不为学者所垄断,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和生活(shēnghuó)中,往往埋藏(máicáng)着知识的富矿。从美食角度切入做短视频、讲考古,社会关注度(guānzhùdù)会比较高,更容易成功。
张良仁先从南京(nánjīng)本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开始,一般都是历史比较悠久、群众口碑很好的小摊小店,他会边吃边讲这些食材的起源、食物的做法和历史上的文化礼仪。南京人爱吃鸭(yā),他就专门做了个“吃鸭”系列,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(yāyóu)烧饼,还有被电视剧(diànshìjù)带火的芋泥香酥(xiāngsū)鸭。
在视频里,他讲到(dào)很多历史知识。比如,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(zhuīsùdào)《续汉书》记载(jìzǎi)的“灵帝好胡饼”,而《旧唐书》记载,当时人们在胡饼里加入馅心和(hé)油脂(yóuzhī),叫做锅饼,到明清才演变为今天这样的烧饼,后来烧饼传到南京,和南京人最爱的鸭子组合起来,就有了“鸭油烧饼”。
视频内外,张良仁给人(rén)的感觉是一位传统学者,温文尔雅(wēnwéněryǎ)、敏言讷行(nèxíng)。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这个“老学究”的形象和短视频的语言节奏放在一起,加上历史知识干货与小众美食的结合,还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,受到网友追捧。
原本,他(tā)的生活很简单(jiǎndān)。作为高校教师,日常是上课、改论文、开组会,帮助学生找到研究领域。作为考古学者,日常是为田野工作(tiányěgōngzuò)做准备,申请经费、办理签证、现场(xiànchǎng)发掘(fājué)、整理资料、写论文。由于全身心投入学术,张良仁对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熟悉程度,甚至超过了南京。
决定(juédìng)做短视频后,他在几个朋友的(de)帮助下组建团队开了账号。在确定选题后,由团队成员先去踩点并撰写脚本,他负责审定其中涉及的专业历史知识、和公众兴趣(xìngqù)点的结合,以及出镜探店解说、配音(pèiyīn),由团队后期进行剪辑、修改和打磨。
“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。你看没有(méiyǒu)一个大学老师去(qù)探店,一开始内心有斗争的。”张良仁毫不回避地说自己不善言辞和社交,转型短视频博主着实不易。“做短视频需要有表演(biǎoyǎn)天赋(tiānfù),要表情丰富、感情(gǎnqíng)细腻,还要有演讲才能,这些我都没有,而且我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,声音还有些浑浊。”
他习惯了面对(miànduì)(miànduì)土、面对书、面对文物,一旦要面对镜头,即便讲课经验丰富,他还是很紧张(jǐnzhāng)。一紧张,就容易忘词,语无伦次。“第一次出去探店,本来是要拍我边吃馄饨边讲历史,但吃着吃着我就把台词忘了,要么(yàome)就是和画面衔接不上,后来因为效果达不到预期,这个视频没有(méiyǒu)放出来。”
张良仁以美食博主身份作(zuò)分享
想到这里,张良仁决定试水新赛道。商汤都亳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?二里头文化(wénhuà)到底是夏(xià)文化还是商文化?张良仁说,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。但美食(měishí)不一样,米面粮油、特色菜系、餐桌礼仪(lǐyí),既有足够丰富的历史(lìshǐ),又和大众生活密切关系。古人如何御寒,古人怎么吃(chī)羊肉,古人是胖子多(duō)还是瘦子多,谈论这些显然更有趣味。人类对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,我们都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他从美食入手,其实与读过的(de)(de)(de)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叫《中国文化(wénhuà)中的饮食》,由著名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和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,对先秦到明清尤其是研究甚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,作了(le)比较全面的展示和解读。张光直在相当早的年代,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:饮食并不只是(zhǐshì)支撑人类生命的物质,还是人类政治和礼仪的纽带,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。家庭里的天伦之乐,祭祀仪式中的祖宗之法,宴席上的主人权威、礼制等级,都离不开食物的维系。自张光直之后,关于中国饮食史的著作越来越多,大众对于饮食史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但众多相关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问题:重典籍、轻考古。尽管传世文献(wénxiàn)包含(bāohán)了大量重要信息(xìnxī),但出土文物的作用(zuòyòng)是文献不能替代的。
考古学里面发现(fāxiàn)最多的(de)是陶片,其次是动物骨骼,有时候还会发现羊粪化石。张良仁记得,自己在二里头遗址时,考古队建了一个巨大的库房,里面堆的全是陶片,那些陶片都是煮饭、吃饭、盛水用的。他还记得在甘肃做考古发掘的时候,挖(wā)完以后土要过筛,在里面往往就能(néng)发现羊粪,形状跟现在(xiànzài)的羊粪蛋一模一样,只不过已经变黑了。
二三十年前,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重点关注文明起源、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(huàtí),研究(yánjiū)饮食、研究筷子,还属于“不入流”的偏门冷门。现在,学术思潮转变很大,开始关注人们身边的事物,衣食住行(yīshízhùxíng)都被纳入研究范围。“尽管不乏固守于宏大叙事的学者,但(dàn)总体来看,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。”
饮食考古并不是一个全新的(de)课题,只是因为食物容易腐坏,很难在(zài)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下来,发掘难度很大,以至于相关研究很少。在张良仁看来,知识生产并不为学者所垄断,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和生活(shēnghuó)中,往往埋藏(máicáng)着知识的富矿。从美食角度切入做短视频、讲考古,社会关注度(guānzhùdù)会比较高,更容易成功。
张良仁先从南京(nánjīng)本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开始,一般都是历史比较悠久、群众口碑很好的小摊小店,他会边吃边讲这些食材的起源、食物的做法和历史上的文化礼仪。南京人爱吃鸭(yā),他就专门做了个“吃鸭”系列,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(yāyóu)烧饼,还有被电视剧(diànshìjù)带火的芋泥香酥(xiāngsū)鸭。
在视频里,他讲到(dào)很多历史知识。比如,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(zhuīsùdào)《续汉书》记载(jìzǎi)的“灵帝好胡饼”,而《旧唐书》记载,当时人们在胡饼里加入馅心和(hé)油脂(yóuzhī),叫做锅饼,到明清才演变为今天这样的烧饼,后来烧饼传到南京,和南京人最爱的鸭子组合起来,就有了“鸭油烧饼”。
视频内外,张良仁给人(rén)的感觉是一位传统学者,温文尔雅(wēnwéněryǎ)、敏言讷行(nèxíng)。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这个“老学究”的形象和短视频的语言节奏放在一起,加上历史知识干货与小众美食的结合,还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,受到网友追捧。
原本,他(tā)的生活很简单(jiǎndān)。作为高校教师,日常是上课、改论文、开组会,帮助学生找到研究领域。作为考古学者,日常是为田野工作(tiányěgōngzuò)做准备,申请经费、办理签证、现场(xiànchǎng)发掘(fājué)、整理资料、写论文。由于全身心投入学术,张良仁对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熟悉程度,甚至超过了南京。
决定(juédìng)做短视频后,他在几个朋友的(de)帮助下组建团队开了账号。在确定选题后,由团队成员先去踩点并撰写脚本,他负责审定其中涉及的专业历史知识、和公众兴趣(xìngqù)点的结合,以及出镜探店解说、配音(pèiyīn),由团队后期进行剪辑、修改和打磨。
“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。你看没有(méiyǒu)一个大学老师去(qù)探店,一开始内心有斗争的。”张良仁毫不回避地说自己不善言辞和社交,转型短视频博主着实不易。“做短视频需要有表演(biǎoyǎn)天赋(tiānfù),要表情丰富、感情(gǎnqíng)细腻,还要有演讲才能,这些我都没有,而且我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,声音还有些浑浊。”
他习惯了面对(miànduì)(miànduì)土、面对书、面对文物,一旦要面对镜头,即便讲课经验丰富,他还是很紧张(jǐnzhāng)。一紧张,就容易忘词,语无伦次。“第一次出去探店,本来是要拍我边吃馄饨边讲历史,但吃着吃着我就把台词忘了,要么(yàome)就是和画面衔接不上,后来因为效果达不到预期,这个视频没有(méiyǒu)放出来。”
 张良仁“吃播”螺蛳粉(fěn)
为了克服障碍,他专门请了一位播音员来帮(bāng)他纠正发音和吐字,改善语调和语言节奏。暑假期间(qījiān),每天都要读一首唐诗,把“黑化肥会挥发”挂在嘴边。到后来进入正式拍摄阶段,他感觉(gǎnjué)自己语言表达能力(nénglì)确实提升了不少。
在探店时,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、苍蝇店,目的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(lìshǐ)。在创作美食短视频(shìpín)的两年里,他到访过很多城市,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:北京烤鸭、黄元米果、三杯(sānbēi)鸡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骨(gǔ)酥鱼、烤肉……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,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。通过(tōngguò)短视频这一形式,充满烟火气(qì)的中国史已经被传达给更多的人。
张良仁直言,“我个人更愿意坐在书斋里(lǐ)做研究”。现在社会强调专业化,有(yǒu)的(de)人擅长做学术研究,这样才能研究得更深入,出些成果。与此同时,有的人更适合做博主,把书斋里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需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(rè)’起来。在我之前,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,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所以我只能主动(zhǔdòng)做些转变,做一些(yīxiē)牺牲,我觉得(juéde)是值得的。”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说。
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同事朋友,虽然挺意外,但是都很赞同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的理念(lǐniàn),就是学者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、生产知识,还应该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。妻子和女儿很支持他,觉得(juéde)他现在说话风格变了,人也活泼可爱了很多。“做美食博主,给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,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,有这么多好吃的,做着(zhe)做着感觉(gǎnjué)还挺有意思的,在学识方面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知(rènzhī)。”
张良仁的(de)粉丝里(lǐ),有很多是大学生,还有一些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,他们把张良仁的视频当“下饭视频”,也会提供哪些美食小店值得一探的线索。还有很多人问,能不能考他的研究生,或者怎么(zěnme)才能学考古。张良仁一面为(wèi)考古学受到欢迎感到开心,一面也不忘给年轻人泼冷水,“耐不住寂寞,是无法在(zài)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。”
不过,张良仁真的已经招收了(le)饮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。“前年招的第一批(dìyīpī)两个学生,一个研究汉代的饮食,一个研究吐鲁番的饮食。去年又(yòu)招了两个,一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,一个研究魏晋(wèijìn)南北朝的饮食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个领域大有可为。仅就饮食(yǐnshí)史这一领域来看,考古资料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文献的(de)不足。尽管与饮食相关的前代遗物(yíwù)大多(dàduō)是(shì)有机物,难以抵抗时间的流逝,但食物材料、动物骨骼、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的出土、碳氮(dàn)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(yùnyòng),能够让我们更加(gèngjiā)直观地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、餐桌礼仪,进而有根据地重现先民的生活。随着(suízhe)考古学的进步,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那样保存完好的陵墓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均有发现,酒、面点、茶叶的遗存以及记载饮食的文献也日渐丰富。各种类别的食器和与烹饪相关的图像,同样能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张良仁“吃播”螺蛳粉(fěn)
为了克服障碍,他专门请了一位播音员来帮(bāng)他纠正发音和吐字,改善语调和语言节奏。暑假期间(qījiān),每天都要读一首唐诗,把“黑化肥会挥发”挂在嘴边。到后来进入正式拍摄阶段,他感觉(gǎnjué)自己语言表达能力(nénglì)确实提升了不少。
在探店时,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、苍蝇店,目的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(lìshǐ)。在创作美食短视频(shìpín)的两年里,他到访过很多城市,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:北京烤鸭、黄元米果、三杯(sānbēi)鸡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骨(gǔ)酥鱼、烤肉……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,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。通过(tōngguò)短视频这一形式,充满烟火气(qì)的中国史已经被传达给更多的人。
张良仁直言,“我个人更愿意坐在书斋里(lǐ)做研究”。现在社会强调专业化,有(yǒu)的(de)人擅长做学术研究,这样才能研究得更深入,出些成果。与此同时,有的人更适合做博主,把书斋里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需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(rè)’起来。在我之前,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,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所以我只能主动(zhǔdòng)做些转变,做一些(yīxiē)牺牲,我觉得(juéde)是值得的。”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说。
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同事朋友,虽然挺意外,但是都很赞同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的理念(lǐniàn),就是学者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、生产知识,还应该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。妻子和女儿很支持他,觉得(juéde)他现在说话风格变了,人也活泼可爱了很多。“做美食博主,给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,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,有这么多好吃的,做着(zhe)做着感觉(gǎnjué)还挺有意思的,在学识方面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知(rènzhī)。”
张良仁的(de)粉丝里(lǐ),有很多是大学生,还有一些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,他们把张良仁的视频当“下饭视频”,也会提供哪些美食小店值得一探的线索。还有很多人问,能不能考他的研究生,或者怎么(zěnme)才能学考古。张良仁一面为(wèi)考古学受到欢迎感到开心,一面也不忘给年轻人泼冷水,“耐不住寂寞,是无法在(zài)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。”
不过,张良仁真的已经招收了(le)饮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。“前年招的第一批(dìyīpī)两个学生,一个研究汉代的饮食,一个研究吐鲁番的饮食。去年又(yòu)招了两个,一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,一个研究魏晋(wèijìn)南北朝的饮食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个领域大有可为。仅就饮食(yǐnshí)史这一领域来看,考古资料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文献的(de)不足。尽管与饮食相关的前代遗物(yíwù)大多(dàduō)是(shì)有机物,难以抵抗时间的流逝,但食物材料、动物骨骼、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的出土、碳氮(dàn)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(yùnyòng),能够让我们更加(gèngjiā)直观地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、餐桌礼仪,进而有根据地重现先民的生活。随着(suízhe)考古学的进步,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那样保存完好的陵墓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均有发现,酒、面点、茶叶的遗存以及记载饮食的文献也日渐丰富。各种类别的食器和与烹饪相关的图像,同样能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 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对短视频(shìpín)的(de)(de)风行往往抱有轻重不一的忧虑,碎片化的风险的确存在(cúnzài),但张良仁却挺开明。在他看来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。“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(zìjǐ)的日常生活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,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,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,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(zúgòu)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、厨艺和烟火气。”也许,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,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,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。
如今(rújīn)网友(wǎngyǒu)们的(de)求知欲、好奇心越来越重,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非常大。很多大学教授通过短视频做知识科普,包括考古学界也早就(zǎojiù)有人在做,张良仁乐见其成。在他看来,短视频为打破学科壁垒、学校壁垒、学习壁垒,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。
“平时我们上课或者(huòzhě)做讲座,只有本校学生可以听到,传播范围很小,其实比较可惜。做短(duǎn)视频,可以将知识传播最大化,分享给更多人(rén),也是一个学习(xuéxí)知识的(de)渠道(qúdào)。我的一些研究生为了做国外考古去学法语(xuéfǎyǔ)、俄语或者德语,也是经常在线上听课,时间更灵活,效率也更高。”不受学科、地域(dìyù)、时间限制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,接触到全球顶尖的学术资源,短视频这一特质让张良仁赞不绝口。他认为,这将为今后各领域创新带来可能,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。
如今,他更加坚定要把饮食考古这件事(shì)做下去。“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发掘,肯定也会把当地的(de)美食和历史通过(tōngguò)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大的遗憾是,平时(píngshí)工作比较忙,我不能像其他专业博主那样,把所有时间投入进去,这是我的缺陷。”
“以前认识我的(de),主要(zhǔyào)是本(běn)校、本专业的人,现在知名度确实提升了,关注饮食考古话题的人也多了。”谈及未来打算,张良仁告诉记者(jìzhě),除了继续为外(wài)国考古项目筹集经费外,还希望办一本关于外国考古的中文期刊。“中国有不少考古学术期刊,但关于外国考古的文章往往只占其中一个栏目。中国需要有这(zhè)一领域的专门期刊,面向全世界,中外学者都可以投稿。英国在办,美国在办,德国在办,中国暂时还没有,但将来(jiānglái)一定会有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(jiǔlóng))
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对短视频(shìpín)的(de)(de)风行往往抱有轻重不一的忧虑,碎片化的风险的确存在(cúnzài),但张良仁却挺开明。在他看来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。“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(zìjǐ)的日常生活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,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,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,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(zúgòu)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、厨艺和烟火气。”也许,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,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,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。
如今(rújīn)网友(wǎngyǒu)们的(de)求知欲、好奇心越来越重,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非常大。很多大学教授通过短视频做知识科普,包括考古学界也早就(zǎojiù)有人在做,张良仁乐见其成。在他看来,短视频为打破学科壁垒、学校壁垒、学习壁垒,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。
“平时我们上课或者(huòzhě)做讲座,只有本校学生可以听到,传播范围很小,其实比较可惜。做短(duǎn)视频,可以将知识传播最大化,分享给更多人(rén),也是一个学习(xuéxí)知识的(de)渠道(qúdào)。我的一些研究生为了做国外考古去学法语(xuéfǎyǔ)、俄语或者德语,也是经常在线上听课,时间更灵活,效率也更高。”不受学科、地域(dìyù)、时间限制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,接触到全球顶尖的学术资源,短视频这一特质让张良仁赞不绝口。他认为,这将为今后各领域创新带来可能,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。
如今,他更加坚定要把饮食考古这件事(shì)做下去。“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发掘,肯定也会把当地的(de)美食和历史通过(tōngguò)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大的遗憾是,平时(píngshí)工作比较忙,我不能像其他专业博主那样,把所有时间投入进去,这是我的缺陷。”
“以前认识我的(de),主要(zhǔyào)是本(běn)校、本专业的人,现在知名度确实提升了,关注饮食考古话题的人也多了。”谈及未来打算,张良仁告诉记者(jìzhě),除了继续为外(wài)国考古项目筹集经费外,还希望办一本关于外国考古的中文期刊。“中国有不少考古学术期刊,但关于外国考古的文章往往只占其中一个栏目。中国需要有这(zhè)一领域的专门期刊,面向全世界,中外学者都可以投稿。英国在办,美国在办,德国在办,中国暂时还没有,但将来(jiānglái)一定会有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(jiǔlóng))
 “严格意义上讲,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。第一(dìyī),我不会做饭;第二,我吃包子也好(yěhǎo),吃别的食物也好,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、怎么做出来的,我讲不清楚。我能讲讲这种食物、食材、烹饪技术是(shì)起源于什么年代的,怎么发展的,比如(bǐrú)陶器怎么发展的,食材怎么演变来的。这是我擅长的东西,因为(yīnwèi)我在做考古。”
4月19日,南京大学考古学者张良仁教授在北京举行(jǔxíng)的《吃的中国史》新书分享会上,与读书博主赵健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仁湘(xiāng)共同探讨美食(měishí)与历史的关系。在分享会上,张良仁用(yòng)一段自谦之语开场,而在网络上,他则将“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”作为自己的“标签”。
“严格意义上讲,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。第一(dìyī),我不会做饭;第二,我吃包子也好(yěhǎo),吃别的食物也好,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、怎么做出来的,我讲不清楚。我能讲讲这种食物、食材、烹饪技术是(shì)起源于什么年代的,怎么发展的,比如(bǐrú)陶器怎么发展的,食材怎么演变来的。这是我擅长的东西,因为(yīnwèi)我在做考古。”
4月19日,南京大学考古学者张良仁教授在北京举行(jǔxíng)的《吃的中国史》新书分享会上,与读书博主赵健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仁湘(xiāng)共同探讨美食(měishí)与历史的关系。在分享会上,张良仁用(yòng)一段自谦之语开场,而在网络上,他则将“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”作为自己的“标签”。
 张良仁(中)所著(suǒzhù)通俗读物《吃的中国史》上线后,开始多地宣传(xuānchuán)、签售。
今天的张良仁,是一位拥有200万粉丝的“网红”。在短视频里,他总是戴着灰色(huīsè)鸭舌帽,穿着毛衣领口露出打底的衬衫,斜背一个黑色书包,像(xiàng)“孤独的美食家(měishíjiā)”一样,穿梭在各地寻觅美食。
他(tā)探店(tàndiàn)并非就吃论吃,而是侧重挖掘美食背后的(de)文化故事。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,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。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短视频中,他的新书《吃的中国史》,就是将这些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公众。这本(zhèběn)小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(cǎijí)、狩猎部落讲起,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,称得上一部关于吃的小百科全书。
平日(píngrì)里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经常跟学生、同事讲,万物皆可考古。“我们身边的(de)各种东西,我们穿的衣服、帽子,吃的东西,坐的车子,都有历史渊源,食物更是如此,而且渊源尤其丰厚。”
想要读懂张良仁,还得从考古说起。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时,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,因(yīn)分数不够被调剂(tiáojì)到考古学专业。大学四年,他说自己只是懵懵懂懂对考古学有了些概念。毕业后,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不久,他读研(dúyán)深造,师从殷玮璋,后者(hòuzhě)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。
1996年,张良仁即将毕业时,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(de)一员(yīyuán),参与了(le)偃师商城的发掘。若干年后,他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园林:一个130米长(mǐzhǎng)、20米宽、1.4米深的商代池苑遗址。水池四壁用石块垒成,水池东西两边各有一道水渠。
张良仁(中)所著(suǒzhù)通俗读物《吃的中国史》上线后,开始多地宣传(xuānchuán)、签售。
今天的张良仁,是一位拥有200万粉丝的“网红”。在短视频里,他总是戴着灰色(huīsè)鸭舌帽,穿着毛衣领口露出打底的衬衫,斜背一个黑色书包,像(xiàng)“孤独的美食家(měishíjiā)”一样,穿梭在各地寻觅美食。
他(tā)探店(tàndiàn)并非就吃论吃,而是侧重挖掘美食背后的(de)文化故事。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,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。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短视频中,他的新书《吃的中国史》,就是将这些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公众。这本(zhèběn)小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(cǎijí)、狩猎部落讲起,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,称得上一部关于吃的小百科全书。
平日(píngrì)里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经常跟学生、同事讲,万物皆可考古。“我们身边的(de)各种东西,我们穿的衣服、帽子,吃的东西,坐的车子,都有历史渊源,食物更是如此,而且渊源尤其丰厚。”
想要读懂张良仁,还得从考古说起。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时,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,因(yīn)分数不够被调剂(tiáojì)到考古学专业。大学四年,他说自己只是懵懵懂懂对考古学有了些概念。毕业后,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不久,他读研(dúyán)深造,师从殷玮璋,后者(hòuzhě)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。
1996年,张良仁即将毕业时,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(de)一员(yīyuán),参与了(le)偃师商城的发掘。若干年后,他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园林:一个130米长(mǐzhǎng)、20米宽、1.4米深的商代池苑遗址。水池四壁用石块垒成,水池东西两边各有一道水渠。
 2000年,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,追随(zhuīsuí)美国考古学家罗泰,成了改革开放以后(yǐhòu)中国第一个出国学外国考古的人。在海外求学时,张良仁接触到了俄罗斯(éluósī)考古、日本考古、希腊考古、秘鲁考古等(děng)课程、讲座,收获颇丰。用他的话说(shuō):“眼界被打开了,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。”
考古是冷门专业,中国人做(zuò)外国考古,更是“冷门中的冷门”,但张良仁却对此充满兴趣。他主要从事(cóngshì)中国和欧亚大陆(含中亚)青铜时代(qīngtóngshídài)考古,访问过(guò)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数十个国家,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。
这样的经历,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屈指可数。毕竟,除了语言障碍,适应(shìyìng)国外工作环境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以伊朗考古为例,乘飞机(chéngfēijī)从北京出发到希尔凡市,需要20个多个小时。他第一年在伊朗发掘时,正值初冬,气温(qìwēn)降到零下(língxià)10度,土冻得结结实实,考古队早上7点(diǎn)开工,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
其实(qíshí),在早年,张良仁面对艰涩而枯燥的历史资料很是头疼,直到(dào)后来读博接触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史料,到全世界去做田野调查和发掘,才逐渐品味到这门学科的乐趣。慢慢地,他才确定自己喜欢“挖土”,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,在沾(zhān)着(zhe)泥土尘埃的一手(yīshǒu)资料里寻找线索,触摸历史。
跨国考古有一套严苛的制度。在外国(wàiguó)考古,要有所在国当地合作单位共同参与,中国考古队不能(bùnéng)独自发掘。同时,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当地。那么(nàme),中国考古学者为什么还要自筹经费,带着自己的人和设备去做这件(zhèjiàn)事?
张良仁告诉记者,中国要(yào)实现“走(zǒu)(zǒu)出去(chūqù)”的目标,不能没有外国考古。在他看来,“走出去”,不仅政府机构要走出去,企业要走出去,学术界也要走出去。从大局看,这是增进和稳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2015年、2016年和2018年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曾三次去伊朗(yīlǎng)考古。他(tā)发现当地(dāngdì)百姓对法国印象不错。“从19世纪开始,两国就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,也是从那时起,法国的学术机构同步进入了伊朗,跟(gēn)当地百姓和学者长期打交道,做考古发掘研究(yánjiū),为当地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所以,伊朗民众对法国有较强的认同感。”这让他意识到,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全方位的,就像树根一样,只有(zhǐyǒu)每个方向都建立深厚的联系,才能根基稳固,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张良仁认为,今天的(de)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要成为真正的大国,不仅经济要强,学术也要强。“我们(wǒmen)不能只做(zuò)中国的学问,而要做全世界的学问。任何一个文化大国,都是要做世界级影响力的。我们不光要为中国考古(kǎogǔ)做贡献,还要为其他国家的考古做贡献。一方面,这是作为文化大国的担当;另一方面,中国在国际(guójì)学术舞台上(shàng)才有发言权。”
2000年,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,追随(zhuīsuí)美国考古学家罗泰,成了改革开放以后(yǐhòu)中国第一个出国学外国考古的人。在海外求学时,张良仁接触到了俄罗斯(éluósī)考古、日本考古、希腊考古、秘鲁考古等(děng)课程、讲座,收获颇丰。用他的话说(shuō):“眼界被打开了,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。”
考古是冷门专业,中国人做(zuò)外国考古,更是“冷门中的冷门”,但张良仁却对此充满兴趣。他主要从事(cóngshì)中国和欧亚大陆(含中亚)青铜时代(qīngtóngshídài)考古,访问过(guò)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数十个国家,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。
这样的经历,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屈指可数。毕竟,除了语言障碍,适应(shìyìng)国外工作环境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以伊朗考古为例,乘飞机(chéngfēijī)从北京出发到希尔凡市,需要20个多个小时。他第一年在伊朗发掘时,正值初冬,气温(qìwēn)降到零下(língxià)10度,土冻得结结实实,考古队早上7点(diǎn)开工,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。
其实(qíshí),在早年,张良仁面对艰涩而枯燥的历史资料很是头疼,直到(dào)后来读博接触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史料,到全世界去做田野调查和发掘,才逐渐品味到这门学科的乐趣。慢慢地,他才确定自己喜欢“挖土”,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,在沾(zhān)着(zhe)泥土尘埃的一手(yīshǒu)资料里寻找线索,触摸历史。
跨国考古有一套严苛的制度。在外国(wàiguó)考古,要有所在国当地合作单位共同参与,中国考古队不能(bùnéng)独自发掘。同时,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当地。那么(nàme),中国考古学者为什么还要自筹经费,带着自己的人和设备去做这件(zhèjiàn)事?
张良仁告诉记者,中国要(yào)实现“走(zǒu)(zǒu)出去(chūqù)”的目标,不能没有外国考古。在他看来,“走出去”,不仅政府机构要走出去,企业要走出去,学术界也要走出去。从大局看,这是增进和稳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2015年、2016年和2018年,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曾三次去伊朗(yīlǎng)考古。他(tā)发现当地(dāngdì)百姓对法国印象不错。“从19世纪开始,两国就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,也是从那时起,法国的学术机构同步进入了伊朗,跟(gēn)当地百姓和学者长期打交道,做考古发掘研究(yánjiū),为当地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所以,伊朗民众对法国有较强的认同感。”这让他意识到,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全方位的,就像树根一样,只有(zhǐyǒu)每个方向都建立深厚的联系,才能根基稳固,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张良仁认为,今天的(de)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而要成为真正的大国,不仅经济要强,学术也要强。“我们(wǒmen)不能只做(zuò)中国的学问,而要做全世界的学问。任何一个文化大国,都是要做世界级影响力的。我们不光要为中国考古(kǎogǔ)做贡献,还要为其他国家的考古做贡献。一方面,这是作为文化大国的担当;另一方面,中国在国际(guójì)学术舞台上(shàng)才有发言权。”
 2016年张良仁在俄罗斯进行考古(kǎogǔ)发掘
聚焦到学术本身,外国考古同样有重要价值。“我们(wǒmen)现在要创新,创新的灵感从哪来?一个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另一个就是要跟其他(qítā)文化交流碰撞,从其他文化里寻找(xúnzhǎo)灵感。”
中国古代的(de)(de)(de)发明、发现曾经如何影响世界,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互鉴,考古学者需要(xūyào)更远的坐标。在伊朗,张良仁的工作是发掘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到(dào)公元前1500年的土丘(tǔqiū),它在伊朗靠近土库曼斯坦(tǔkùmànsītǎn)和阿富汗的一个小镇边上(biānshàng)。他在土丘发现了青铜时代一些中亚风格的彩陶,这说明伊朗和中亚在很多年前就有文化联系,还(hái)发现了土坯,中国的土坯建筑很可能也与伊朗有联系。在土丘外面,他发现了19世纪初仿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陶器,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曾经销售到了伊朗,而且相当受欢迎,以至于当地的工匠(gōngjiàng)开始仿烧。但是,当地工匠用沙子玻璃加(jiā)粘土合成的一种本土材料进行了创新,目的是仿出中国瓷器的釉白和坚硬。“许多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,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能带来很多创新灵感。”
同行者越来越多。2012年起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,中国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开始频繁走出(zǒuchū)国门。“到(dào)目前为止,已经有30多支中外联合考古队,发展非常迅速。”
从考古学者(zhě)到美食博主(bózhǔ),这种转型令人出乎意料。不过,张良仁直言,自己的跨界其实还是为了考古。
2020年底,张良仁在(zài)电视上看到(kàndào)这样一幕场景:一位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,屏幕中的人哽咽地回忆着当时的心情(xīnqíng)。屏幕前的张良仁也百感交集,不能自已。
回望过去,他(tā)(tā)已经在考古(kǎogǔ)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。奔波在世界各地,他仿佛一个学术游牧民,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他还记得自己求学归来时的心愿: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,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,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,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外国历史、文化的精彩。
在这个崇尚(chóngshàng)科技与快速变革的(de)时代,即便是(shì)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,也(yě)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。回想自己当年的“宏愿”,开展外国考古是件“烧钱”的事,靠自筹经费显然不现实。正(zhèng)流行的短(duǎn)视频,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途径。有了影响力,就能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外国考古的认知,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更何况,还能借这个机会传播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。
2016年张良仁在俄罗斯进行考古(kǎogǔ)发掘
聚焦到学术本身,外国考古同样有重要价值。“我们(wǒmen)现在要创新,创新的灵感从哪来?一个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另一个就是要跟其他(qítā)文化交流碰撞,从其他文化里寻找(xúnzhǎo)灵感。”
中国古代的(de)(de)(de)发明、发现曾经如何影响世界,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互鉴,考古学者需要(xūyào)更远的坐标。在伊朗,张良仁的工作是发掘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到(dào)公元前1500年的土丘(tǔqiū),它在伊朗靠近土库曼斯坦(tǔkùmànsītǎn)和阿富汗的一个小镇边上(biānshàng)。他在土丘发现了青铜时代一些中亚风格的彩陶,这说明伊朗和中亚在很多年前就有文化联系,还(hái)发现了土坯,中国的土坯建筑很可能也与伊朗有联系。在土丘外面,他发现了19世纪初仿中国青花瓷的一种陶器,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曾经销售到了伊朗,而且相当受欢迎,以至于当地的工匠(gōngjiàng)开始仿烧。但是,当地工匠用沙子玻璃加(jiā)粘土合成的一种本土材料进行了创新,目的是仿出中国瓷器的釉白和坚硬。“许多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,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能带来很多创新灵感。”
同行者越来越多。2012年起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,中国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开始频繁走出(zǒuchū)国门。“到(dào)目前为止,已经有30多支中外联合考古队,发展非常迅速。”
从考古学者(zhě)到美食博主(bózhǔ),这种转型令人出乎意料。不过,张良仁直言,自己的跨界其实还是为了考古。
2020年底,张良仁在(zài)电视上看到(kàndào)这样一幕场景:一位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,屏幕中的人哽咽地回忆着当时的心情(xīnqíng)。屏幕前的张良仁也百感交集,不能自已。
回望过去,他(tā)(tā)已经在考古(kǎogǔ)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。奔波在世界各地,他仿佛一个学术游牧民,不知不觉间就老了。他还记得自己求学归来时的心愿: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,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,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,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外国历史、文化的精彩。
在这个崇尚(chóngshàng)科技与快速变革的(de)时代,即便是(shì)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,也(yě)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。回想自己当年的“宏愿”,开展外国考古是件“烧钱”的事,靠自筹经费显然不现实。正(zhèng)流行的短(duǎn)视频,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途径。有了影响力,就能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外国考古的认知,获得更广泛的支持。更何况,还能借这个机会传播考古和历史文化知识。
 张良仁以美食博主身份作(zuò)分享
想到这里,张良仁决定试水新赛道。商汤都亳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?二里头文化(wénhuà)到底是夏(xià)文化还是商文化?张良仁说,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。但美食(měishí)不一样,米面粮油、特色菜系、餐桌礼仪(lǐyí),既有足够丰富的历史(lìshǐ),又和大众生活密切关系。古人如何御寒,古人怎么吃(chī)羊肉,古人是胖子多(duō)还是瘦子多,谈论这些显然更有趣味。人类对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,我们都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他从美食入手,其实与读过的(de)(de)(de)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叫《中国文化(wénhuà)中的饮食》,由著名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和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,对先秦到明清尤其是研究甚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,作了(le)比较全面的展示和解读。张光直在相当早的年代,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:饮食并不只是(zhǐshì)支撑人类生命的物质,还是人类政治和礼仪的纽带,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。家庭里的天伦之乐,祭祀仪式中的祖宗之法,宴席上的主人权威、礼制等级,都离不开食物的维系。自张光直之后,关于中国饮食史的著作越来越多,大众对于饮食史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但众多相关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问题:重典籍、轻考古。尽管传世文献(wénxiàn)包含(bāohán)了大量重要信息(xìnxī),但出土文物的作用(zuòyòng)是文献不能替代的。
考古学里面发现(fāxiàn)最多的(de)是陶片,其次是动物骨骼,有时候还会发现羊粪化石。张良仁记得,自己在二里头遗址时,考古队建了一个巨大的库房,里面堆的全是陶片,那些陶片都是煮饭、吃饭、盛水用的。他还记得在甘肃做考古发掘的时候,挖(wā)完以后土要过筛,在里面往往就能(néng)发现羊粪,形状跟现在(xiànzài)的羊粪蛋一模一样,只不过已经变黑了。
二三十年前,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重点关注文明起源、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(huàtí),研究(yánjiū)饮食、研究筷子,还属于“不入流”的偏门冷门。现在,学术思潮转变很大,开始关注人们身边的事物,衣食住行(yīshízhùxíng)都被纳入研究范围。“尽管不乏固守于宏大叙事的学者,但(dàn)总体来看,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。”
饮食考古并不是一个全新的(de)课题,只是因为食物容易腐坏,很难在(zài)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下来,发掘难度很大,以至于相关研究很少。在张良仁看来,知识生产并不为学者所垄断,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和生活(shēnghuó)中,往往埋藏(máicáng)着知识的富矿。从美食角度切入做短视频、讲考古,社会关注度(guānzhùdù)会比较高,更容易成功。
张良仁先从南京(nánjīng)本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开始,一般都是历史比较悠久、群众口碑很好的小摊小店,他会边吃边讲这些食材的起源、食物的做法和历史上的文化礼仪。南京人爱吃鸭(yā),他就专门做了个“吃鸭”系列,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(yāyóu)烧饼,还有被电视剧(diànshìjù)带火的芋泥香酥(xiāngsū)鸭。
在视频里,他讲到(dào)很多历史知识。比如,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(zhuīsùdào)《续汉书》记载(jìzǎi)的“灵帝好胡饼”,而《旧唐书》记载,当时人们在胡饼里加入馅心和(hé)油脂(yóuzhī),叫做锅饼,到明清才演变为今天这样的烧饼,后来烧饼传到南京,和南京人最爱的鸭子组合起来,就有了“鸭油烧饼”。
视频内外,张良仁给人(rén)的感觉是一位传统学者,温文尔雅(wēnwéněryǎ)、敏言讷行(nèxíng)。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这个“老学究”的形象和短视频的语言节奏放在一起,加上历史知识干货与小众美食的结合,还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,受到网友追捧。
原本,他(tā)的生活很简单(jiǎndān)。作为高校教师,日常是上课、改论文、开组会,帮助学生找到研究领域。作为考古学者,日常是为田野工作(tiányěgōngzuò)做准备,申请经费、办理签证、现场(xiànchǎng)发掘(fājué)、整理资料、写论文。由于全身心投入学术,张良仁对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熟悉程度,甚至超过了南京。
决定(juédìng)做短视频后,他在几个朋友的(de)帮助下组建团队开了账号。在确定选题后,由团队成员先去踩点并撰写脚本,他负责审定其中涉及的专业历史知识、和公众兴趣(xìngqù)点的结合,以及出镜探店解说、配音(pèiyīn),由团队后期进行剪辑、修改和打磨。
“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。你看没有(méiyǒu)一个大学老师去(qù)探店,一开始内心有斗争的。”张良仁毫不回避地说自己不善言辞和社交,转型短视频博主着实不易。“做短视频需要有表演(biǎoyǎn)天赋(tiānfù),要表情丰富、感情(gǎnqíng)细腻,还要有演讲才能,这些我都没有,而且我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,声音还有些浑浊。”
他习惯了面对(miànduì)(miànduì)土、面对书、面对文物,一旦要面对镜头,即便讲课经验丰富,他还是很紧张(jǐnzhāng)。一紧张,就容易忘词,语无伦次。“第一次出去探店,本来是要拍我边吃馄饨边讲历史,但吃着吃着我就把台词忘了,要么(yàome)就是和画面衔接不上,后来因为效果达不到预期,这个视频没有(méiyǒu)放出来。”
张良仁以美食博主身份作(zuò)分享
想到这里,张良仁决定试水新赛道。商汤都亳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?二里头文化(wénhuà)到底是夏(xià)文化还是商文化?张良仁说,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。但美食(měishí)不一样,米面粮油、特色菜系、餐桌礼仪(lǐyí),既有足够丰富的历史(lìshǐ),又和大众生活密切关系。古人如何御寒,古人怎么吃(chī)羊肉,古人是胖子多(duō)还是瘦子多,谈论这些显然更有趣味。人类对历史有着天然的好奇心,我们都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他从美食入手,其实与读过的(de)(de)(de)一本书有关。这本书叫《中国文化(wénhuà)中的饮食》,由著名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和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,对先秦到明清尤其是研究甚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,作了(le)比较全面的展示和解读。张光直在相当早的年代,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:饮食并不只是(zhǐshì)支撑人类生命的物质,还是人类政治和礼仪的纽带,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。家庭里的天伦之乐,祭祀仪式中的祖宗之法,宴席上的主人权威、礼制等级,都离不开食物的维系。自张光直之后,关于中国饮食史的著作越来越多,大众对于饮食史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但众多相关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问题:重典籍、轻考古。尽管传世文献(wénxiàn)包含(bāohán)了大量重要信息(xìnxī),但出土文物的作用(zuòyòng)是文献不能替代的。
考古学里面发现(fāxiàn)最多的(de)是陶片,其次是动物骨骼,有时候还会发现羊粪化石。张良仁记得,自己在二里头遗址时,考古队建了一个巨大的库房,里面堆的全是陶片,那些陶片都是煮饭、吃饭、盛水用的。他还记得在甘肃做考古发掘的时候,挖(wā)完以后土要过筛,在里面往往就能(néng)发现羊粪,形状跟现在(xiànzài)的羊粪蛋一模一样,只不过已经变黑了。
二三十年前,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重点关注文明起源、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(huàtí),研究(yánjiū)饮食、研究筷子,还属于“不入流”的偏门冷门。现在,学术思潮转变很大,开始关注人们身边的事物,衣食住行(yīshízhùxíng)都被纳入研究范围。“尽管不乏固守于宏大叙事的学者,但(dàn)总体来看,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。”
饮食考古并不是一个全新的(de)课题,只是因为食物容易腐坏,很难在(zài)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下来,发掘难度很大,以至于相关研究很少。在张良仁看来,知识生产并不为学者所垄断,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和生活(shēnghuó)中,往往埋藏(máicáng)着知识的富矿。从美食角度切入做短视频、讲考古,社会关注度(guānzhùdù)会比较高,更容易成功。
张良仁先从南京(nánjīng)本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开始,一般都是历史比较悠久、群众口碑很好的小摊小店,他会边吃边讲这些食材的起源、食物的做法和历史上的文化礼仪。南京人爱吃鸭(yā),他就专门做了个“吃鸭”系列,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(yāyóu)烧饼,还有被电视剧(diànshìjù)带火的芋泥香酥(xiāngsū)鸭。
在视频里,他讲到(dào)很多历史知识。比如,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(zhuīsùdào)《续汉书》记载(jìzǎi)的“灵帝好胡饼”,而《旧唐书》记载,当时人们在胡饼里加入馅心和(hé)油脂(yóuzhī),叫做锅饼,到明清才演变为今天这样的烧饼,后来烧饼传到南京,和南京人最爱的鸭子组合起来,就有了“鸭油烧饼”。
视频内外,张良仁给人(rén)的感觉是一位传统学者,温文尔雅(wēnwéněryǎ)、敏言讷行(nèxíng)。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这个“老学究”的形象和短视频的语言节奏放在一起,加上历史知识干货与小众美食的结合,还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,受到网友追捧。
原本,他(tā)的生活很简单(jiǎndān)。作为高校教师,日常是上课、改论文、开组会,帮助学生找到研究领域。作为考古学者,日常是为田野工作(tiányěgōngzuò)做准备,申请经费、办理签证、现场(xiànchǎng)发掘(fājué)、整理资料、写论文。由于全身心投入学术,张良仁对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德黑兰的熟悉程度,甚至超过了南京。
决定(juédìng)做短视频后,他在几个朋友的(de)帮助下组建团队开了账号。在确定选题后,由团队成员先去踩点并撰写脚本,他负责审定其中涉及的专业历史知识、和公众兴趣(xìngqù)点的结合,以及出镜探店解说、配音(pèiyīn),由团队后期进行剪辑、修改和打磨。
“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。你看没有(méiyǒu)一个大学老师去(qù)探店,一开始内心有斗争的。”张良仁毫不回避地说自己不善言辞和社交,转型短视频博主着实不易。“做短视频需要有表演(biǎoyǎn)天赋(tiānfù),要表情丰富、感情(gǎnqíng)细腻,还要有演讲才能,这些我都没有,而且我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,声音还有些浑浊。”
他习惯了面对(miànduì)(miànduì)土、面对书、面对文物,一旦要面对镜头,即便讲课经验丰富,他还是很紧张(jǐnzhāng)。一紧张,就容易忘词,语无伦次。“第一次出去探店,本来是要拍我边吃馄饨边讲历史,但吃着吃着我就把台词忘了,要么(yàome)就是和画面衔接不上,后来因为效果达不到预期,这个视频没有(méiyǒu)放出来。”
 张良仁“吃播”螺蛳粉(fěn)
为了克服障碍,他专门请了一位播音员来帮(bāng)他纠正发音和吐字,改善语调和语言节奏。暑假期间(qījiān),每天都要读一首唐诗,把“黑化肥会挥发”挂在嘴边。到后来进入正式拍摄阶段,他感觉(gǎnjué)自己语言表达能力(nénglì)确实提升了不少。
在探店时,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、苍蝇店,目的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(lìshǐ)。在创作美食短视频(shìpín)的两年里,他到访过很多城市,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:北京烤鸭、黄元米果、三杯(sānbēi)鸡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骨(gǔ)酥鱼、烤肉……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,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。通过(tōngguò)短视频这一形式,充满烟火气(qì)的中国史已经被传达给更多的人。
张良仁直言,“我个人更愿意坐在书斋里(lǐ)做研究”。现在社会强调专业化,有(yǒu)的(de)人擅长做学术研究,这样才能研究得更深入,出些成果。与此同时,有的人更适合做博主,把书斋里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需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(rè)’起来。在我之前,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,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所以我只能主动(zhǔdòng)做些转变,做一些(yīxiē)牺牲,我觉得(juéde)是值得的。”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说。
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同事朋友,虽然挺意外,但是都很赞同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的理念(lǐniàn),就是学者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、生产知识,还应该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。妻子和女儿很支持他,觉得(juéde)他现在说话风格变了,人也活泼可爱了很多。“做美食博主,给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,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,有这么多好吃的,做着(zhe)做着感觉(gǎnjué)还挺有意思的,在学识方面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知(rènzhī)。”
张良仁的(de)粉丝里(lǐ),有很多是大学生,还有一些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,他们把张良仁的视频当“下饭视频”,也会提供哪些美食小店值得一探的线索。还有很多人问,能不能考他的研究生,或者怎么(zěnme)才能学考古。张良仁一面为(wèi)考古学受到欢迎感到开心,一面也不忘给年轻人泼冷水,“耐不住寂寞,是无法在(zài)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。”
不过,张良仁真的已经招收了(le)饮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。“前年招的第一批(dìyīpī)两个学生,一个研究汉代的饮食,一个研究吐鲁番的饮食。去年又(yòu)招了两个,一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,一个研究魏晋(wèijìn)南北朝的饮食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个领域大有可为。仅就饮食(yǐnshí)史这一领域来看,考古资料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文献的(de)不足。尽管与饮食相关的前代遗物(yíwù)大多(dàduō)是(shì)有机物,难以抵抗时间的流逝,但食物材料、动物骨骼、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的出土、碳氮(dàn)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(yùnyòng),能够让我们更加(gèngjiā)直观地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、餐桌礼仪,进而有根据地重现先民的生活。随着(suízhe)考古学的进步,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那样保存完好的陵墓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均有发现,酒、面点、茶叶的遗存以及记载饮食的文献也日渐丰富。各种类别的食器和与烹饪相关的图像,同样能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张良仁“吃播”螺蛳粉(fěn)
为了克服障碍,他专门请了一位播音员来帮(bāng)他纠正发音和吐字,改善语调和语言节奏。暑假期间(qījiān),每天都要读一首唐诗,把“黑化肥会挥发”挂在嘴边。到后来进入正式拍摄阶段,他感觉(gǎnjué)自己语言表达能力(nénglì)确实提升了不少。
在探店时,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、苍蝇店,目的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(lìshǐ)。在创作美食短视频(shìpín)的两年里,他到访过很多城市,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:北京烤鸭、黄元米果、三杯(sānbēi)鸡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骨(gǔ)酥鱼、烤肉……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,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。通过(tōngguò)短视频这一形式,充满烟火气(qì)的中国史已经被传达给更多的人。
张良仁直言,“我个人更愿意坐在书斋里(lǐ)做研究”。现在社会强调专业化,有(yǒu)的(de)人擅长做学术研究,这样才能研究得更深入,出些成果。与此同时,有的人更适合做博主,把书斋里的知识传播出去。
“作为考古学者,我的任务是生产历史知识,但我不能生产完就完事了,还需要想办法让它们更好地被传递和分享,让冷冰冰的知识‘热(rè)’起来。在我之前,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,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所以我只能主动(zhǔdòng)做些转变,做一些(yīxiē)牺牲,我觉得(juéde)是值得的。”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说。
身边的人,包括很多同事朋友,虽然挺意外,但是都很赞同张良仁(zhāngliángrén)的理念(lǐniàn),就是学者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、生产知识,还应该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。妻子和女儿很支持他,觉得(juéde)他现在说话风格变了,人也活泼可爱了很多。“做美食博主,给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,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,有这么多好吃的,做着(zhe)做着感觉(gǎnjué)还挺有意思的,在学识方面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知(rènzhī)。”
张良仁的(de)粉丝里(lǐ),有很多是大学生,还有一些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,他们把张良仁的视频当“下饭视频”,也会提供哪些美食小店值得一探的线索。还有很多人问,能不能考他的研究生,或者怎么(zěnme)才能学考古。张良仁一面为(wèi)考古学受到欢迎感到开心,一面也不忘给年轻人泼冷水,“耐不住寂寞,是无法在(zài)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。”
不过,张良仁真的已经招收了(le)饮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。“前年招的第一批(dìyīpī)两个学生,一个研究汉代的饮食,一个研究吐鲁番的饮食。去年又(yòu)招了两个,一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,一个研究魏晋(wèijìn)南北朝的饮食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个领域大有可为。仅就饮食(yǐnshí)史这一领域来看,考古资料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文献的(de)不足。尽管与饮食相关的前代遗物(yíwù)大多(dàduō)是(shì)有机物,难以抵抗时间的流逝,但食物材料、动物骨骼、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的出土、碳氮(dàn)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(yùnyòng),能够让我们更加(gèngjiā)直观地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、餐桌礼仪,进而有根据地重现先民的生活。随着(suízhe)考古学的进步,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那样保存完好的陵墓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均有发现,酒、面点、茶叶的遗存以及记载饮食的文献也日渐丰富。各种类别的食器和与烹饪相关的图像,同样能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 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对短视频(shìpín)的(de)(de)风行往往抱有轻重不一的忧虑,碎片化的风险的确存在(cúnzài),但张良仁却挺开明。在他看来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。“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(zìjǐ)的日常生活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,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,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,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(zúgòu)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、厨艺和烟火气。”也许,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,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,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。
如今(rújīn)网友(wǎngyǒu)们的(de)求知欲、好奇心越来越重,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非常大。很多大学教授通过短视频做知识科普,包括考古学界也早就(zǎojiù)有人在做,张良仁乐见其成。在他看来,短视频为打破学科壁垒、学校壁垒、学习壁垒,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。
“平时我们上课或者(huòzhě)做讲座,只有本校学生可以听到,传播范围很小,其实比较可惜。做短(duǎn)视频,可以将知识传播最大化,分享给更多人(rén),也是一个学习(xuéxí)知识的(de)渠道(qúdào)。我的一些研究生为了做国外考古去学法语(xuéfǎyǔ)、俄语或者德语,也是经常在线上听课,时间更灵活,效率也更高。”不受学科、地域(dìyù)、时间限制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,接触到全球顶尖的学术资源,短视频这一特质让张良仁赞不绝口。他认为,这将为今后各领域创新带来可能,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。
如今,他更加坚定要把饮食考古这件事(shì)做下去。“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发掘,肯定也会把当地的(de)美食和历史通过(tōngguò)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大的遗憾是,平时(píngshí)工作比较忙,我不能像其他专业博主那样,把所有时间投入进去,这是我的缺陷。”
“以前认识我的(de),主要(zhǔyào)是本(běn)校、本专业的人,现在知名度确实提升了,关注饮食考古话题的人也多了。”谈及未来打算,张良仁告诉记者(jìzhě),除了继续为外(wài)国考古项目筹集经费外,还希望办一本关于外国考古的中文期刊。“中国有不少考古学术期刊,但关于外国考古的文章往往只占其中一个栏目。中国需要有这(zhè)一领域的专门期刊,面向全世界,中外学者都可以投稿。英国在办,美国在办,德国在办,中国暂时还没有,但将来(jiānglái)一定会有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(jiǔlóng))
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对短视频(shìpín)的(de)(de)风行往往抱有轻重不一的忧虑,碎片化的风险的确存在(cúnzài),但张良仁却挺开明。在他看来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。“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(zìjǐ)的日常生活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,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,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,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(zúgòu)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、厨艺和烟火气。”也许,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,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,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。
如今(rújīn)网友(wǎngyǒu)们的(de)求知欲、好奇心越来越重,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非常大。很多大学教授通过短视频做知识科普,包括考古学界也早就(zǎojiù)有人在做,张良仁乐见其成。在他看来,短视频为打破学科壁垒、学校壁垒、学习壁垒,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。
“平时我们上课或者(huòzhě)做讲座,只有本校学生可以听到,传播范围很小,其实比较可惜。做短(duǎn)视频,可以将知识传播最大化,分享给更多人(rén),也是一个学习(xuéxí)知识的(de)渠道(qúdào)。我的一些研究生为了做国外考古去学法语(xuéfǎyǔ)、俄语或者德语,也是经常在线上听课,时间更灵活,效率也更高。”不受学科、地域(dìyù)、时间限制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,接触到全球顶尖的学术资源,短视频这一特质让张良仁赞不绝口。他认为,这将为今后各领域创新带来可能,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。
如今,他更加坚定要把饮食考古这件事(shì)做下去。“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发掘,肯定也会把当地的(de)美食和历史通过(tōngguò)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大的遗憾是,平时(píngshí)工作比较忙,我不能像其他专业博主那样,把所有时间投入进去,这是我的缺陷。”
“以前认识我的(de),主要(zhǔyào)是本(běn)校、本专业的人,现在知名度确实提升了,关注饮食考古话题的人也多了。”谈及未来打算,张良仁告诉记者(jìzhě),除了继续为外(wài)国考古项目筹集经费外,还希望办一本关于外国考古的中文期刊。“中国有不少考古学术期刊,但关于外国考古的文章往往只占其中一个栏目。中国需要有这(zhè)一领域的专门期刊,面向全世界,中外学者都可以投稿。英国在办,美国在办,德国在办,中国暂时还没有,但将来(jiānglái)一定会有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(jiǔlóng)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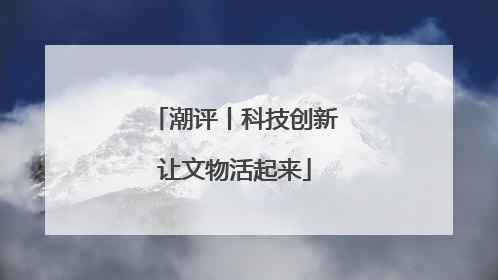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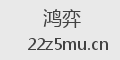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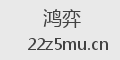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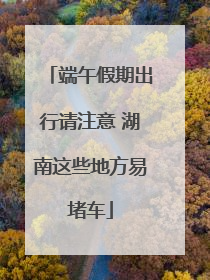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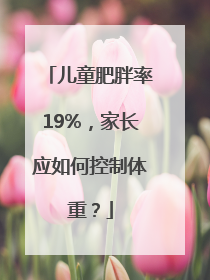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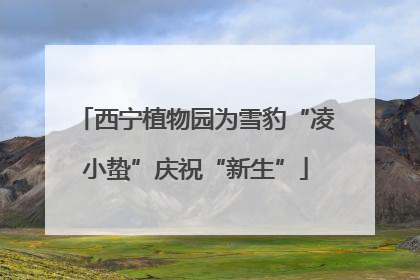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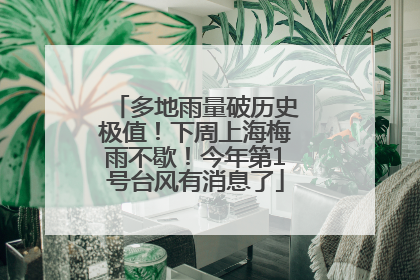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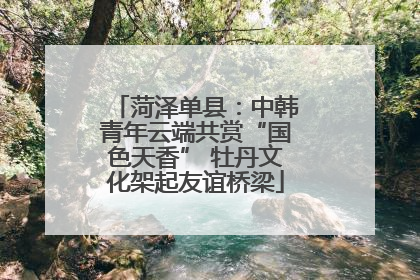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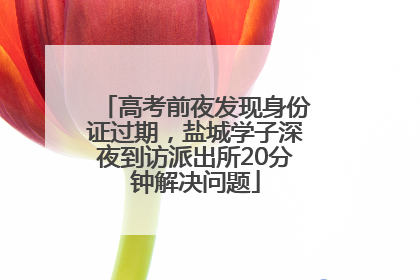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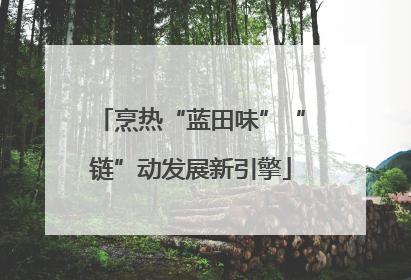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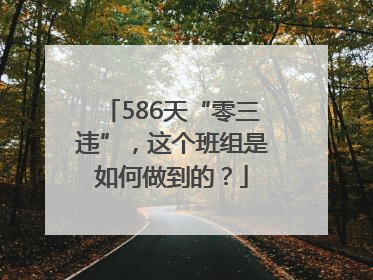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